来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鲍雨萌
3月,罗永浩宣布签约抖音,转型为职业网红。 首场直播销量1.1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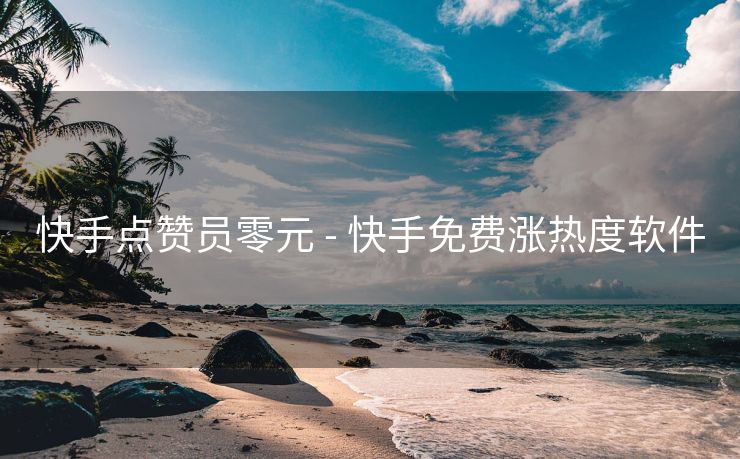
4月,淘宝网红薇娅在直播间以4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火箭。
6月,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直播中创造了65亿的销售奇迹。 单日销售额相当于格力今年一季度总营收的三分之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2.62亿。 在中国就业培训与技术指导中心5月11日发布的新职业信息中,网络营销员职业下的“直播推销员”工种特别引起关注。 直播从未像现在这样流行。
各种带货“神话”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明星涌入直播间。 与此同时,一直备受关注的直播也正在成为虚假流量肆意增长的巨大温床。
在社交平台上,你可以找到大量为抖音、快手等视频直播平台提供数据服务的商家。 成熟的算法程序让机器人用户渗透各大平台,10000次浏览量5元低价出售; 而下游,面子工程、KPI考核、货币福利等各种买家需求,堆积了巨大的泡沫。 ,共同造就了直播流量的虚假繁荣。
“虚假流量生意不会随着互联网而消失。” 一位受访者向记者感叹。
直播流量的虚假繁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淘宝上搜索直播数据,可以发现大量提供数据服务的商家。 不过,从6月份开始,淘宝就开始清理相关商品。 在QQ上,你还可以找到很多以抖音、快手为关键词的用户群体。
记者联系了多家商家,他们均表示可以低价提供点赞、播放、评论、分享等视频和直播相关的数据服务。 以其中之一为例。 在快手上,1万次浏览仅需5元。 15元,可以购买50人在直播间观看一整天。 量大有优惠,20元可以买100人。
单个视频的观看量还很小,一些机构的专业系统已经相当成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有一个号称“80%的短视频营销人员都在使用”的云控系统。 在其宣传介绍中,称其可以“一键开通400个抖音,批量点赞评论,迅速热门”。 “进粉丝、引流量”、“一个人管理上百部云手机”。
“大家都在买数据,如果你不买,你就无法与别人竞争,你就会吃亏。这不是潜规则,但可以说是常态。”行业。” 一位经营网红的MCN机构营销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据了解,带货网红在与品牌公司签约时一般会收取两类费用。 一是坑费,另外还有实际销售的佣金。 直播越来越火,大主播的收费也水涨船高。 据说罗永浩的坑位费高达60万,薇娅、李佳琪的坑位费都在20万以上起步。
很多聘请不起大主播的品牌只能在一些营销公司的推荐下转用小主播。 事实上,小主播的流量非常惨淡。 MCN机构只能靠买流量来向“资助者”付款。
另一种采购需求是场景支撑。 一位卖流量的商家告诉记者,这种流量多见于线下经营活动、开店等,“撑场面,买点流量,让领导、老板好看”。
“品牌现在更加注重销售转化率,光是刷流量已经没那么有用了,平台的羊毛也不是那么好收的,不排除有人开始刷单,然后退货。” 一位MCN机构工作人员透露,直播刚开始时,平台有引流奖励。 购买流量可以让您在平台上获得更好的推荐位置。 只要有一点转化,就能获得不错的回报。 “但是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它就没那么有用了。 如果做得太过分,销售数据就跟不上,品牌就会发现这一点。”
一些平台已经开始追查、拦截虚假流量。 淘宝上一位名叫鑫汇科技的商家告诉记者,目前只能接受淘宝直播、腾讯直播、看店直播等平台的订单。 “快手和抖音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很容易被发现。”
一位抖音认证商家表示,一个视频内容在抖音获得高人气后,可能会被平台认可并推送到更多人的时间线,但抖音的算法也会发现那些异常的内容。 流量会增加,从而降低视频的权重,这会严重限制用户的流量,但得不偿失。
不仅小主播存在欺诈行为,就连头部主播也成为利益驱动下虚假流量的受益者。
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些大牌网红的话语权更强,不会按照常规方式抽取佣金。 某知名网红曾为某服装品牌做过直播,要求按订单量而非实际成交额结算。
“只要消费者在直播间将该品牌的衣服加入购物车,即使最终没有完成交易,主播也能拿佣金。对于这样的网红公司,找人刷单订单可以带来更大的利润收入。”
快手顶级直播红人二鹿夫妇、辛巴都曾因数据造假被质疑。 在二鹿夫妇的一次直播中,该产品被下架,但销售数字仍在上涨。
“直播市场泡沫很大。” 电商策略分析师李成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泡沫不仅体现在头部网红经纪公司的估值泡沫上,还体现在“大家都在带货” ”。 “疯狂。
流量诈骗背后的技术攻防
胡晓文(化名)曾是一家外企的算法工程师。 她从事媒体行业的数据分析,帮助品牌公司评估媒体投资的真实效果。 其中,如何剥离注水数据是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技术难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发现了市场上购买网络流量的巨大需求。 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承担一些“私人工作”,为造假者编写程序和算法。
“作弊的技术手段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场景在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技术运用的空间越来越大。” 胡晓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网络上的假订单需求最早开始出现在电商行业。 商家通过创建虚假订单和购买好评来提高平台上展示的产品排名。 类似的技术在社交平台上催生了网络巨魔、僵尸粉丝、受控评论和其他形式。 后来羊毛党出现,接管了各种互联网应用。 近两年风头正劲的直播形成了新的流量入口,也产生了大量的购买流量需求。
“如果通过刷单实现的收入比刷单本身便宜,就会有人薅羊毛,这件事就会一直在网络上存在。” 胡晓文说,她接触到的买家大多是明星经纪公司和品牌公司。 据记者了解,随着网红经济的兴起,MCN机构是直播领域流量买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虚假流量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于专门刷单的廉价劳动力,更大一部分来自于机器程序。 目前,这个产业链已经非常成熟,分工明确。 像胡晓文这样的技术团队就相当于程序工厂,还有专门招人的销售链条。 甚至还细分为专门的配套服务,比如从事收集验证码的公司,以满足完成大量账户登录的验证码要求。 “猫池”也成为假流量生产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是电脑刷赞,几乎是免费的,租个服务器就行了快手免费涨热度软件,包括电费、网费,每个月的费用也就两三百块。只要程序做得好,一台电脑产生的流量一天的房间可能是几亿,几千万,甚至上亿。” 胡小文告诉记者,“电脑可以更好地完成加好友、加关注、点赞等,但总体来说,发表评论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但与收入相比,就很有限了。在一些四、四五线城市,一个月能招到两三千人,而且还有大量学生打工。”
流量诈骗的过程是诈骗程序与互联网平台风控之间的攻防战。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不断被优化。 胡晓文说,“比如一些电商平台上的虚假交易,早期的流程就是不断地在电脑上切换账户买东西,很容易被平台发现。所以慢慢就变成了招募大量的人。”借用电脑安装软件不需要他们自己操作,当他们使用电脑时,软件会自动在后台下订单。”
甚至还出现了针对短视频流量诈骗的特殊病毒。
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移动安全工程师张建国(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传统的流氓利用自己的手机增加流量不同,该病毒通过感染其他设备来完成点击、浏览、此类病毒的隐蔽性更强,因为它们感染的大多是自然用户,不易被平台发现,不像机器人巨魔的特点可以被清晰识别。
“之前各大厂商都报告过类似的攻击事件,随着防御的升级,近期此类病毒的情况已经有所减少。” 张建国表示,短视频流量病毒往往捆绑在手机和电脑上常用的工具软件中,由用户安装。 会被感染。 中毒后,受感染设备会在受控的情况下在后台访问指定链接,增加视频流量。
胡小文认为,刷单程序的原则是寻找平台的漏洞,形成有效的算法策略,而不踩平台的红线。 “对于平台来说,点击数据是无法造假的,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点击,这是平台可以控制的,只是这个人是谁而已。对于平台来说,追踪的成本很高,而且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时间管它,这些地方都是它的漏洞,我们会从漏洞中寻找空间。”
技术的攻击和防御往往需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了解平台的算法是第一步。 因此,反向推平台的算法是假流量程序背后的重要环节快手免费涨热度软件,并且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分工。 该环节由胡晓文负责。
“比如某视频平台对视频的评价有一个衡量参数叫流行度,这个流行度是怎么计算的?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数据分析复制底层公式,然后找到这个公式的漏洞。找到之后漏洞的话,用机器或者人力的手段‘杀掉它’。”胡晓文说。
与简单的点赞、关注、评论等已有标准解决方案和市场定价的服务相比,部分买家的需求越来越要求精准,并趋向于收费较高的定制服务。 胡小文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在前面提到的视频平台上,要将某个视频的热度提升20%,我们首先要了解其背后的原理和算法,然后将20%的热度转化为具体的点击和评论。 、弹幕、转发、浏览指标,然后找到相应的人力资源来完成这个量化的任务”。
在胡晓文看来,技术攻防战的核心不在于被平台发现,而在于满足付费的人。 “总体来说,我们正走在风险控制的边缘。”
在胡晓文之前的工作经历中,她曾为多家互联网平台提供风控方面的战略咨询,但他发现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愿意升级风控。 “很多平台关心的可能不是数据的真实性,而是如何让财报好看。一旦平台把所有数据都挤出来,产品表现可能会很难看,这是平台本身不想要的。”事实上,平台更多的是在平衡好数据更重要还是收入更重要。”
视频刷单存在法律风险
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流量诈骗行业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2019年7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一起流量诈骗案。
2017年,爱奇艺在后台数据分析中发现,部分视频内容出现了访问量急剧上升后趋于稳定的异常情况。 经核实,爱奇艺发现异常数据来自杭州飞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为视频网站提供视频刷赞服务的公司。 仅2017年2月1日至同年6月1日,飞艺公司对爱奇艺网站的访问日志总计约9.5亿条。 爱奇艺认为,飞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破坏了视频行业公平竞争秩序。
这也是国内首例因视频网站“刷量”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案件。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指出,本案中,虚构视频点击行为实质上强化了相关经营者及公众对虚构视频点击的质量、播放量、关注度等的错误认识。 ,起到了吸引消费者的目的。 因此,虚构视频点击量属于相关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的一部分,应按虚假宣传处理。
据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捏造视频点击量的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游云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来看,直播中购买虚假流量的一方首先构成对其品牌和赞助商的欺诈;其次构成对直播间购买虚假流量的行为。 其次,是对平台内其他主播及其他内容提供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这种行为破坏了直播平台的机制和生态,也违反了平台规定。
“流量诈骗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长期存在的痼疾,其中滋生的违法产品对健康的网络生态有明显的损害,其中最大的损害是对产业生态本身。视频平台及其背后的投资者也是受害者。” 游云婷说道。
- - - - 结尾 - - - -
其他用户正在观看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