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解释为何3亿人被遗忘的文章。
1. 起源
6月初,一篇名为《底层的残酷故事:一款视频软件在中国农村》(以下简称“故事”)的文章在朋友圈频繁转发。文章严肃地提到了一款名为“快手”的应用,报道说快手是一款“低俗、简单、粗暴”的社交“视频软件”,却精准地再现了农村日渐荒凉的生活,尤其是日渐加剧的城乡二元分化。文章迅速引发讨论,一时间,呼声、感叹、质疑声此起彼伏。但正如我所料,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约72小时后,这些讨论就沉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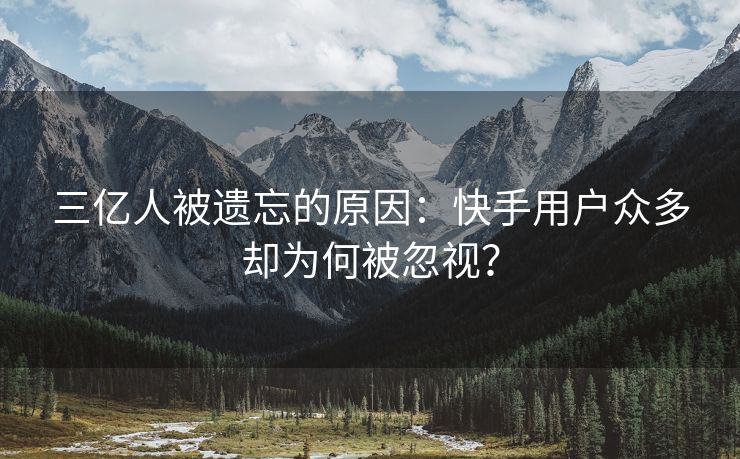
快手讨论沉沦了?这真的很不正常!我想说三个事实:
1、快手用户数超过3亿,相当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总人口数。同时,快手是中国第四大最受欢迎的移动应用,每日活跃用户超过1000万。在这个全民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颗可以轻松挤进全球社交产品前10名的明星。
作为一款成功的社交产品,快手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同时,它的主要用户是此前在城市媒体上消失的“农村人”。
2:《故事》这篇文章出炉前几天,我去清华大学上班。走出清华东门后,惊讶地看到清华科技园上快手的橙色标志已经取代了网易标志。清华科技园是帝都IT界一个图腾般的办公地点,Google、EMC、Adobe、搜狐等大牌云集于此。快手的姿态显然不是要告别。换句话说,3亿用户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3:更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居然“遗忘”了快手!
据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在《故事》之后,关于这款产品的微信介绍文章只有五篇,观点也都比较肤浅。与此同时,大多数精明的投资者对快手一无所知,聪明的互联网同行也沉默不语,喜欢大新闻的媒体人更是傻眼——总之,快手从都市白领的朋友圈里“消失”了,被遗忘了!
2. 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快手究竟从何而来?我简单转载了《8月18日因频繁更新朋友圈引发争议的快手:一个没人听说过的APP居然有3亿用户!》、《天通苑的张小龙》两篇文章的报道:
2011.3 GIF快手诞生
2012.11 GIF快手从纯工具应用转型为短视频社区
2013.10 GIF快手转型后,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长都有明显提升。
2014年春节后,快手流量开始暴增,大量东北用户加入快手
2014.11 GIF快手更名为快手
2015.6快手日用户上传量突破260万,用户数突破1亿
2016.2快手用户规模突破3亿
上述报告乍一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如果结合互联网的现实,其中的矛盾就令人震惊。
2011年,在风起云涌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款不起眼的APP诞生了。它的发展很快遭遇了瓶颈,于是创始团队做出了进军社交领域的“艰难决定”。2013年底到2014年初,数据的增长证明了这次转型的正确性,同时也让快手踩上了短视频潮流的风口浪尖。此后,快手一路高歌猛进,用户量超过3亿。按照互联网正史的书写,快手创始团队现在应该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参加各种行业论坛和峰会,或者去硅谷接受风投大神们的接见——他们“应该”被人们羡慕嫉妒恨。然而,只是理所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成为现实。比如,在我打出这篇文字的时候,快手老板程一笑的微博粉丝只有702个!
3亿用户的重量不必多言,但让人疑惑的是,媒体不但没有大规模曝光快手,反而陷入了令人羞耻的低迷!
另外,如果接受前面几篇文章的观点,我们仍然无法解释这个核心问题:
为什么快手上的人大多都是农村人?
因为业界普遍认识到,广大农村地区受限于网络流量稀缺、人口分散等客观条件,不利于互联网普及。
为了消除上述疑虑,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的线索继续追查。
我觉得在官方对快手崛起的历史记录中,遗漏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那就是2014年春节过后,快手的流量开始爆发,大量东北地区的用户加入。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手都知道,网络流量的变化其实是日常人口变化在网络上的体现,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即使远行千里,也要回家与家人团聚。
春运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2014年的春运从1月16日开始,到2月24日结束,共运送旅客36亿多人次,是特定时间发生的人类迁徙奇观。春运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大批农村人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纷纷涌入城市,成为服务员、建筑工人、保安、快递员等职业。
我的猜测是,2014年春节期间,这些农民工把快手带回了家乡,他们春节回乡之后,地理上的分离再次割断了大城市与三四五线城市、农村的联系,让快手得以在这些地方不受干扰地渗透、疯狂生长。
有时候我们感觉移动互联网社区在激烈的斗争,但那可能只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可能只是在中关村,甚至只是在你的朋友圈里。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在这片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样的猜测似乎太过仓促,因为没有实际研究。对此,本文认为,将农民工视为快手的“传染源”,至少可以解释两种极其关键的情况:
1、快手为何在2014年春节后爆红?
2、快手用户为何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 ——因为就近打工是人的天性,北方的务工者自然会选择快手的发源地北京。
3、农民工VS白领?
前面提到,快手是一款由“农民工”推动的产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农民工是谁?他们有什么特点?如何定义他们?似乎很难下结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农民工”是与“白领”相对立的一群人。首先,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农民工”的特点。其次,与互联网创投圈相关的人都是白领。将他们与“农民工”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拥有3亿用户的快手被遗忘。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2011年秋天,我住在北京北部的“沉睡之城”天通苑。这里是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小区,从空中俯瞰,这里的全景简直“壮观”!(图)
据说当年程义孝也住在这里。
在天通苑打过工的农民工都知道,这里有多“热闹”,尤其是上下班的五号线沿线。
早上八九点,天通苑五号线地铁站人潮拥挤,比上海世博园还要热闹:各色人等挤在一起快手刷双击,同时被推入地铁;牙膏味、口臭味、香水味、鸡蛋饼味等混合在一起,着实让男女老少心惊胆寒。
地铁五号线从天通苑出发,很快就到达惠新西街南口站——这个站很有意思。
惠新西街南口站是生活北京与工作北京的换乘站,此站衔接纵贯帝都南北、东西的5号线、10号线。
早高峰,从5号线天通苑站挤进来的乘客,在惠新西街南口站挤出去,奔向10号线,他们大多的目的地是西边的中关村、东边的国贸。
2011年,中关村大卖场还如火如荼,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因为电商的兴起而濒临破产,国贸正成为世界顶级中央商务区的代名词。
当天通园居民在惠新西街南口换乘火车时,按照“超市式”和“写字楼式”分成两拨,“老派”打工者往西走,而“洋派”打扮的白领则往东走。
这两类人,对于任何有正常理性的人来说,都是很容易区分的。或者说,他们的差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是什么将这两组人区分开来呢?
首先不会是衣着,这个太外在了,我们无法单凭衣着就能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定位。
其次,以小区来判断并不合适,为了避开北京中心城区疯狂的房价,选择天通苑等经济适用小区是大多数人的合理选择。
最后,用收入水平来判断也不对。根据招聘网站的数据,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6947元,扣除正常的衣食住行支出后,这个数字并不多。同时,虽然北京、上海农民工整体收入略低于白领,但大多数有技能的农民工收入可能超过白领平均水平。
那么,这两类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两类人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期待。
这种“自我期待”的差异,会进一步表现为双方“身份”乃至对外“感受”的差异。
对于白领来说,融入城市、留在城市是当务之急。选择成为白领,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份“白领”的工作,更是选择了一整套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了在大城市有车有房生活,白领们必须接受大城市的象征性制度:城市户籍、五险一金、办公室政治等等。这个制度就像是城市生活中的客观标准,白领们必须学会迎合它,才能在未来成为所谓的“中产”。
但农民工的期望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城市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中转站——农民工在这里挣钱谋生,就是为了回到家乡过上好日子;至于在大城市买房、还房贷,他们并不关心。换言之,农民工对于自己能否融入大城市似乎比较冷漠。
白领阶层的自我期待导致他们全盘接受城市生活的符号体系,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忽视农民工和他们的世界,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生存无关。这种漠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为歧视。比如,兼职服务员在工作中就经常会遭遇城市人的冷眼甚至鄙视。
正如《天通苑张小龙》一文所引述:“有人评论说,打开快手,你看到的是一个失败者的世界,失败者的世界。他们没有钱,没有文化,他们有自己的品味,虽然这些品味不是很高。这些在县城、农村,或者城市角落的人,也需要一个满足他们品味的互联网平台。”
这条多次提到“品味”二字的评论,十分嚣张,表面上是在谈论快手,实则在用鄙夷的眼光评论农民工和他们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白领对于大城市的符号没有选择权,他们的话题基本固定,比如时尚、健身、乐活、星座;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充满了各种符号,比如各种品牌、互联网、马云等。
但无一例外,这些符号都是由引领“品味”的“精英们”创造并定义的——它们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即将被灌输到白领阶层的头脑中。
在谈论和操纵这些符号的过程中,白领完成了自我认同。但这只是一场幻想游戏。这背后是白领“脱颖而出”和“与众不同”的焦虑。因此,白领实际上是一个被城市符号彻底驯服的群体,他们的优越感具有主观虚构的意义。
白领阶层的这种自我优越感,使得农民工沦为沉默的背景——他们被白领阶层遗忘在“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中。
换言之快手刷双击,白领阶层对农民工存在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冷漠,这种冷漠是为了欺骗自己,巩固自我认同,从而切断与陌生事物的联系。
我想,这才是快手从都市媒体和白领朋友圈中消失的真正原因。
虽然被驯化必然导致创造力和文化修养的缺失,但白领的优越感依然让他们自诩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特权阶层。对于白领来说,评判日常生活中事物的“品味”和“价值”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最多只接受上层“精英”的影响,而对于农民工的创作,他们本能地选择忽视、遗忘,甚至彻底鄙视。
在白领们的眼中,农民工所做的工作是照本宣科、粗糙野蛮的,是一群没有“前途”的人,是所谓的“底层”。
在白领们的眼中,农民工根本不配拥有创造力,他们只会创作出让人尴尬、恶心的内容。
在白领们的眼中,快手映照出的是一个可悲、可笑、低俗的世界——猴子的世界。
白领阶层所接受的符号体系决定了他们或多或少会这么看待。
虽然有些农民工爱炫耀自己的车和包,尖脸剪刀手自拍,确实显得“低俗”和“不时尚”,但他们并没有被城市符号彻底驯服(PS:白领不炫耀自己的车和包,如果你公开这样做,别人会认为你是微商,白领在做这些事情时会展现出他们驯服的“优雅”和技巧)。因为大城市忽视农民工,农民工本身也没有强烈的融入大城市的愿望,所以他们自然会创造出自己不同于白领世界的符号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农民工在快手上近乎疯狂地上传内容,这些内容很容易就能得到几千个赞。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他们在家乡的亲朋好友,都生活在一个网络流量相对稀缺的环境中,疯狂上传的背后有着毋庸置疑的强大的生产和消费动机。
这意味着,在白领眼中被视为背景工作者的农民工,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并非沉默的,他们充满活力,是具有强烈欲望的消费者。事实上,农民工甚至已经超越了消费者的范畴,正如在快手上看到的,他们成为了自我符号的创造者,在白领世界之外自给自足。
农民工在快手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符号体系,白领则沉入了既定的符号体系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才是具有创造性“活力”的人。
4.快手爆发
农民工为何更有活力?
1、快手一直在打造自己的热门符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打开快手会一头雾水,因为不知道快手里面的套路到底是什么。比如“双击评论666”这句快手很火,这是快手自己的符号。
快手上的流行趋势也是日新月异,玩法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两三个月前,“爆裆”视频在快手上就很火。我的看法是,“爆裆”和过年放鞭炮有关。随着春节渐行渐远,“爆裆”玩法必然会过时。
快手已经有了自己的封闭花园,来客都是被白领遗忘的“农村人”。正如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快手和它的人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脱离一二线城市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也是客观存在的。”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其他主流社交产品里的明星在快手什么都不是。
以上几点说明快手是一个完整、自给自足的社交系统。
2:快手内容简直就是类型片。就像一般的电影可以分为公路片、警匪片、恐怖片、科幻片等类型一样,快手上的内容也可以这样分类。
从类型上看,快手内容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才艺表演或者各种爆炸性的“杂耍”表演,比如《物语》里提到的各种“自虐视频”、“低俗表演”等等。
还有一种摄影是针对日常生活的,就跟拍普通的照片一样,不加任何滤镜,只是如实呈现“事实”。
但关于生活拍摄这个题材,我还是要说几句:因为不是表演,而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所以有新闻价值。快手因为有大量这样的内容,成为了中国最真实的类YouTube产品。
3:上述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题材,实际上却产生了关联,并产生了第三种类型,本文称之为“舞台新闻”。由于是交叉的产物,这类题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选秀节目的杂技性,二是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新闻价值。
“为拍戏而创作的新闻”彻底颠覆了观众的眼光,真假难辨。
比如《物语》中提到的快手阿姨事件:据新闻报道,警方怀疑该阿姨受他人控制,在快手上发布各种吃“恶心”东西的视频。但怀疑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阿姨亲口表示是自愿的!
当然,快手阿姨是否被人控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演变成“社会治安事件”,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图)
澎湃新闻还有更劲爆的消息:
不自杀就不会死,“小丑恶作剧”已被警方发现,并已上通缉令。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拍摄行为实际上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
这三个例子说明:
在快手上,戏剧性拍摄与新闻报道的界限被人为模糊。新闻不再是突发的客观事件,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杂耍”表演,其引发的影响成为新的新闻。换言之,人为制造的“社保案件”或“新闻”成为快手“选秀”的一部分,成为获取点赞手段。
为什么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其根本原因?
因为当用户拍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内心已经原谅了一切危害,处于一种“入戏”的状态。什么社会保障、责任感,都点赞666一样双击放一边了。虚拟即是现实,现实即是虚拟!
快手的高速发展,让其日益成为“主流城市价值观”和主流社交网络之外的“无人区”,拥有一整套完整的符号生产和消费能力,自给自足,形成闭环。同时,快手的影响力也充分延伸到现实,不断制造事件和流行符号。
所以,快手已经不再是《故事》里提到的那个“视频软件”,而是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快速成长的、独立的社交平台!它将创造一整套的表达体系,甚至一整套的价值观!这里面的内容,每分每秒都在反向强化着它用户的日常行为!而无论你是否忽视,它的用户就在你身边!
五、结论
“太真实了……”当我在餐厅里把这篇文章的要点告诉我的朋友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呃”的表情。我的朋友确实是城市白领,但他思想开明,睿智,爱读书,受过良好教育,不装腔作势。
他可以接受快手有独立的社交体系,但不快手快手在农民工群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让他去问服务员。于是,他叫来一个服务员,是河北的一个小伙子。我问他知不知道快手。他说他经常用,上面的东西挺有意思。朋友又问他老乡、同事用不用。他点头,说都用。朋友这时完全沉默了。
吃完饭,送朋友去地铁站,道别,他说今晚会认真看快手,明天跟我说感受,然后转身融入人群。
这时,我突然想起2011年我在天通苑上下班的情景。
生活日复一日,每天五点半过后,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们都结束了一天的战斗,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有的走出国贸的写字楼,有的拉下超市的百叶窗,挤进地铁,在惠新西街南口换乘时再相见。地铁里,白领和打工者默默地走在一起,疲惫感弥漫着整个天通苑。手机闪烁的屏幕终于暗了下来。
住在“睡城”天通苑的人一定不知道,这里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夜幕之下,北京渐渐陷入沉寂,但谁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两个北京!中国呢?会不会有两个中国?我不知道该不该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天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昨晚在快手上逐一验证了我的观点后,他百感交集,一夜没睡。
七天后,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最近租房见了不少房产中介,无一例外,都是用快手……
不信你有机会可以去问。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