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做自然科普已经第十一年了,很多人仍然问张晨亮:知道你的花鸟鱼虫的名字有什么用?
文字| 刘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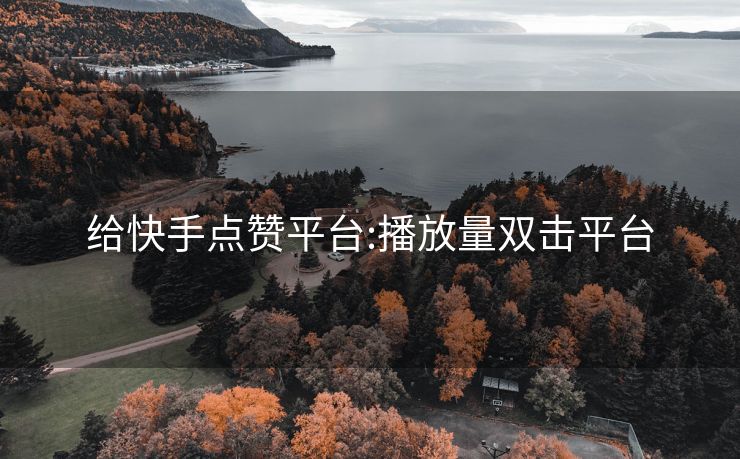
具有“网络意识”的博物学家
现在张晨亮走在街上,总会有人认出他,上至幼儿园的孩子,下至40多岁的中年人。 有时候孩子害羞,家长就会把孩子拉过来要合影:“我们的孩子真喜欢你。”七八年前,他去中学讲课时,心里还暗暗高兴。当一名初中生认出他本人就是“博物学家先生”时。 今年他回到母校中国农业大学讲学。 讲座结束后,十几位本科生亲自过来感谢他,表示因为从小喜欢他的科普,所以现在就读于农业大学。 年初我们在西藏墨脱拍摄时,一名援藏干部告诉张晨亮,他去年观看了他们拍摄的六石滩植物群纪录片后,报名来西藏。 在30分钟的纪录片中,团队介绍了水母雪兔、绿丝绒、贝母以及各种丝蝴蝶。 这些美丽而稀有的生物都生长在海拔4700米、含氧量不足13%的高原上。 。
“我以后吃饭的时候可以指出这种感觉。” 张晨亮开玩笑道。 他的粉丝很多都是孩子,就像《红楼梦》剧组30周年重聚一样。 张晨亮认为,当他70岁、80岁的时候,这些粉丝会把他当成一种童年记忆——张晨亮确实有这个影响力,他的网名是“无限小亮”,而这个粉丝数量互联网各平台ID已突破5000万。
团队拍摄西藏墨脱森林的膜蕨(受访者提供)
2015年,我们第一次采访张晨亮时,他刚刚在网络上出名,没有人知道他的科普工作日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一年,“博物学”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人们加入俱乐部,开始观鸟、赏花、学习辨星座。 张晨亮当时27岁,是《博物》杂志官方微博的唯一编辑。 每天都有大量网友追他,称他为“薄无君”,询问:“这只蜘蛛有毒吗?” “我买了一盆盆栽,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什么鸟?它在我的防盗窗上产卵。”
问答看起来就像脱口秀。 他用平实的语言说话,总是甩掉包袱:
“臭虫卵。不过别害怕,它们已经是空壳了。虫子已经孵化了,到处爬行。”
“三尖蜘蛛,全国那么多,多如苍蝇,一文不值。”
“榆树绿叶甲虫的幼虫以榆树为食,而榆树到处都是,所以也随处可见。很多人问过我,下次请记住,不要再问了。”
“珍珠颈斑鸠喜欢在人的窗台上孵蛋。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半倒的花盆扶正就行了。我看着不舒服。”
张晨亮的科普风格从此就非常明确:先写物种名称,再介绍习性。 最后一句话只是为了好玩。
他从不写拉丁名字,因为普通人无法理解它们。 物种名称也必须放在第一位——如果你说“鸡冠花,红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如果你说“这是红色鸡冠花”,一群人肯定会回答:你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
《无限小亮度》张晨亮(吴家祥 摄)
这些都是网上整理的课程。 张晨亮经常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识别物种,只贴物种名称,不贴别的。 最后只有一两条评论和转发。 “这种鉴定不具有娱乐性,你说人们看你的鉴定真的是为了学习知识吗?其实只是为了好玩,如果达不到这个需求,那我就得改一下,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什么样的文章看了两眼就关掉了?” 张晨亮最想避免的是那种阴险的写作风格:当有人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时,首先要回答“谢谢”,然后继续。 我自己的经历,我二姨的经历,亲爱的,一下子就给你带来了三万年前的经历。 当你开玩笑的时候,你还得在句末写上“(笑)”——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笑,这完全是装腔作势。
“这就像一堵知识墙直接射到我脸上。手机页面上有很多文字,都是很多废话。我必须从文字中挑选出我想要的答案。” 张晨亮表示,寻找答案的过程不应该由读者来完成,而应该由创作者来完成。 很多人说他有“网络感”,善于开玩笑,有幽默感。 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微博也可以称为标准的互联网内容产品:必须清晰,必须读起来过瘾,每一个句子过渡都必须符合逻辑。
2011年刚接手微博官方账号时,张晨亮还是一名实习生。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专业的研究生。 他从小就看《博物志》杂志,一心想经营好微博,留下来当编辑。 到2021年卸任时,张晨亮经营10年的《博物馆杂志》微博粉丝数已从不足2万增至1200万。 这也导致纸质杂志订阅量逆势增长。
在过去的十年里,媒体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纸质杂志早已不再是大众阅读的首选,微博在舆论场上的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让位于短视频。 老牌媒体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受众,科普工作也是如此。
团队在数十米高空拍摄植物学家采集巨树标本(受访者提供)
从学术论文播放量双击平台,到大众纸质杂志,到论坛,再到140字微博,科普的最新渠道在不断变化。 每一次新媒体平台的切换,就会淘汰一批人。 张晨亮出生于1988年,这群“80后”经历了互联网启蒙,刚刚经历了社交媒体的文字时代,现在又开始面对短视频。 “两次革命性的变革,就相当于朝代更迭,这就是英雄出世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适应。”
一开始我真的很不习惯。 2019年底,张晨亮在一个名为“无限小亮每日科普”的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账号。 他仍然以“物种名称-视频介绍-甩掉包袱”的形式发布物种鉴定,每条帖子的时间不到一分钟。
现在看来,效果只是“凑合”——也有老粉丝支持,但评论只有十几条。 观看次数最多的一集是关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当地人在盛夏跳进护城河游泳纳凉。 视频中的河流是美丽的蓝色。 旁白中,张晨亮用北京口音解释道:“我站着看了一会儿,有老人、女人,有大人、有小孩,听说一大早就有上班族从自家门口跳下来。”早上上班的时候,我爬起来上班,没有遇到堵车。”
这期突然火爆,浏览量突破千万,城市游泳话题引来数万条评论。 但张晨亮只去过瑞士一次。 尽管视频很受欢迎,但它并不可持续。 这并不是他最擅长的。
图片@无限小梁的科普日报
短视频会流行什么样的科普内容?
2018年和2019年,张晨亮自己看视频,发现有两类知识视频很受欢迎:一是外国博主讲述俄罗斯超市牛奶多少钱。 这与他拍摄的瑞士人狂泳的照片类似,观众会感到新鲜、大开眼界; 一类是营销号制作的奇特动物,比如“最爱老婆的螃蟹”。 大家看似都在学习知识,但实际上知识是错误的。
六个月后,转折点出现了,张晨亮制作了一段视频,将家里常见的白斑虫子识别为粉红螨虫。 视频中,在朋友家里发现了这种bug。 我发给小亮了。 他用微距镜头放大后发现那是一只螨虫。 他查了螨虫专着,辨认了具体种类,并告诉大家,这种虫子经常在大米、火腿、坚果等表面滋生。 如果家里有羊毛地毯,也容易出现尘螨。 保持通风干燥、多晒太阳、使用除螨剂等都是有效的。
“除了这些知识之外,这本书还教你怎么画螨毛,怎么养螨虫,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就能养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呢?”
本期获得60万点赞,一炮而红。 半个月前,他还在北京拍摄了一期早春的花虫。 他在自家门前的河边拍下了四月份刚刚发芽的花草,并一一介绍了早开的堇菜、榆钱、黄钩虫等。 蝴蝶、菜白蝴蝶、小豆角虫、山桃山杏等,一期集中讨论了十多个品种,浏览量也超过300万。
两个视频走红,张晨亮终于找到了自己擅长的角度:这些东西很常见,但没人知道怎么做。 “它与每个人的生活相关,浓缩且独特。 这是我的方向之一。”
《但是还有书》剧照
2020年4月17日,张晨亮发布近期网络热传的生物鉴定第一期,在4分14秒内密集介绍了12个物种。 多个虚假信息被曝光:网友称自己家门口徒步时遇到的大鸟是生活在非洲的灰冠鹤。 位于石家庄的神秘水下动物实际上是海牛,仅分布在美洲和非洲。 还有一位海上博主惊喜发现的玫瑰蜗牛。 它实际上是一只鹦鹉螺,被博主亲自剥壳、染色并埋葬。 张晨亮模仿营销号的语气:“就是为了让你点击。” 双击添加关注。”
这种密集辟谣、讲笑话的新形式一炮而红。 它被互联网上的人们转载了。 很快就有评论称是从QQ空间——微博、哔哩哔哩、QQ空间等找到的,有人在平台上非法发布了这段视频。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三年后,张晨亮这本《网络热点生物鉴定》已经出版了第49期,每期仍然有全网4000万左右的浏览量,让每一期都火爆。 成为罕见的常青热点。
回想起来,除了博物学知识本身的新鲜感之外,还有一些天时地利的好:虽然2019年开通视频号有点晚了,但几个平台还是有流量支持的。 “如果放在2023年,所有生态位都站稳了脚跟,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你再大的网红,也很难突破。” 另一位是张晨亮的声音,浑厚而不落俗套。 或高或低,听起来都很亲切。 他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北京口音,但并不是那种“嘿!看怎么回事!”的浓重嚣张的北京口音,其实很吸引人。
和微博一样,整个视频的安排其实有着清晰的逻辑线。 每次编辑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这部分工作永远不能外包。
张晨打开了他的点赞页面,随机给我们展示了他点赞视频页面。 当点赞每个视频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安排——
以最新第49期为例。 这期 10 分钟的内容涵盖了十多个物种。 开篇要求你在2秒内快速说出“识别网络上热门生物视频”(如果你说得慢,大家都会标记出来)。 标题越说越有风格,第一个物种已经被提到了,网友们都惊呆了。
第一个物种,最漂亮、最具视觉吸引力。 它是假单胞菌属的棒状蛾。 (大家都会愣一下吧?什么鬼?)
第二个物种应该很有趣。 这是葡萄牙的一个水库,在航拍中它看起来像一条中国龙。 (你必须使用更有趣的东西来留住用户。)
第三种不太有趣,但应该说。 例如,人工沟渠必须为动物留有逃生路线。
第四个物种是另一个新物种。 这是一种猫屎果,也被称为“死人手指”。 (没有干扰,没有小便点。)
第五和第六个物种,会有休息时间谈论热门电视剧中蝴蝶标本剥制术的不正确知识以及可爱的玻利维亚咖喱尾豪猪。 (你不能把所有的刺激都给他,有的物种只是想给人休息一下,这时候弹幕就会少一些。)
第七种、第八种,休息一下之后,还会出现一些比较硬核的生物,不过观众现在应该已经累了。 最后,是时候驳斥经典的“水猴”谣言了,揭秘世界各地的“水猴”谣言,并告诉大家这些神秘的未知生物到底是什么? (此时,大家都兴致勃勃。)
《但是还有书》剧照
“这个结局,相声里叫‘包袱很硬’,是最后一个包袱,说完就下台了。” 张晨亮还利用《水猴》的固定结局来培养粉丝忠诚度,提高视频的完整性。 广播率。
最新一期没有水猴。 这是关于错误的“手指水母进化成人形水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生物进化。 这是短视频平台上热搜的一个笑话。 为了增加流量,营销号自动抓取热搜,然后利用AI自动生成文案、制作视频。 播出时还配上了水母的视频,评论里不少人还真以为进化论被颠覆了。
张晨亮把这样的视频放在最后:这种营销账号自动生成的假视频正在污染我们每天看到的信息。 一些新闻机构不进行调查核实,而是直接抄袭类似视频和照片,制作“松花江出品”巨型立体冰花的假新闻。 它不仅散布虚假新闻,还损害新闻道德和媒体公信力。 这实际上是当前“水猴”谣言的另一种形式。
做科普的意义是什么?
九月初的这个周五,张晨亮一早就来到了单位。 办公室空无一人。 他的所有同事都在家加班修改影片:当天晚上8点播放量双击平台,他们将推出一部半小时的纪录片,专门介绍西藏墨脱的自然生态。 为了这部电影,大家都忙了大半年了。
张晨亮开始制作长纪录片。 现任《博物馆》杂志副主编、中国国家地理综合媒体中心主任。 由于网上说他的方脸像藏狐,融媒体中心的年轻员工就称呼他为“狐狸总监”。
《但是还有书》剧照
长纪录片,这是另一种新的媒体形式。 本期墨脱拍摄到的墨脱杉树、条纹树蛙、圆疣树蛙、藏螳螂、墨脱香蕉……很多都是中国西藏墨脱地区特有的,普通网友无法接触到的。 ,也是一个无法轻易拍摄的物种。
张晨亮在片中担任主持人。 他从山中参天的杜鹃树下走出来,说道:“人走在它的树下,就好像变成了一只昆虫。” 事实上,他在树下走了三四次,我从各个角度都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这句台词在出发前也被导演和他在北京办公室逐句修改过。 到达现场后,我们严格按照剧本计划进行。
这和发微博或者做短视频的个人粗暴的感觉完全不同。 纪录片的拍摄需要至少10人的人力,长途跋涉到野外,要么面临缺氧、酷热潮湿的气候,要么面临各种致命的紧急情况。 最后发现暂时没有精力去现场解释。 张晨亮在镜头前不化妆。 顶多在头上喷点摩丝,防止头发乱飞,在脸上抹点粉,防止发油光。 他穿着一件夹克,直视镜头。 他一开口,依然能听到北京口音,但语气却严肃了许多。
这部长纪录片的拍摄方法是从零开始探索的。 他从2021年开始组建综合媒体中心,招募了十几个人,做了“单位热门同事鉴定”,还参观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大院。 在第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结果时好时坏,有时一段视频会走红。 ,下一张同样的方式拍摄,观看次数莫名其妙,十分惨淡。
35岁的张晨亮承受的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他自己的微博和视频几乎不花钱,但现在一个部门一年要花费几百万的人力物力。 新科普到底应该拍什么? 我们一直在拍摄云南香格里拉的流石海滩和海南的热带雨林。 看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新的路线。 在这一期的墨脱,他们想告诉观众中国最珍贵的地理生态。
《生命的奇迹:墨脱森林》
这是一本视觉杂志,和以前一样,所有物种的排列都有内涵逻辑:首先我问一下,为什么干燥的西藏会有墨脱这样潮湿的地方,演化成大片森林? ?
在这个大问题下,剧组拍摄了杜鹃花、树萝卜,还拍摄了条纹树蛙的卵,这些卵会直接挂在叶子上,不晒干; 拍摄时,鸡蛋会产在竹筒里,流入竹子的眼睛里。 雨水繁殖圆疣树蛙的后代。 最后,用一种昆虫将植物和两栖动物连接在一起,这就是干水蛭。 影片把水蛭章节拍得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渲染了吸血水蛭的恐怖气氛。 影片最后,张晨亮问道,为什么当地有这么多蚂蟥? 说明这里有足够的凶兽支持。
张晨亮表示,纪录片也可以算是一篇文章。 “在短视频主导的世界里,拍纪录片本身就是自杀行为。如果你不把纪录片拍得既有吸引力又不烦人,你整天花钱干什么?”
有观众立即指出,这部影片开头的鹤镜头与BBC的《绿色星球》非常相似,这是市场上最高水平的自然纪录片。 主持人大卫·阿滕伯勒爵士今年已经97岁了。 ,是英国自然纪录片的重要先驱。 他从一台16毫米胶片机开始,制作了BBC第一部海外冒险纪录片。 在接下来的七十多年里,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观众追随他的脚步,探索海洋、森林、冰川和极地,以及用当今最先进的技术拍摄的无数稀有物种。
《绿色星球》剧照
在大卫·爱登堡的纪录片中,他曾介绍过不同的媒体形式给科普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位艺术家首次将鲸鱼的歌声录制成黑胶唱片。 此次公开释放首次让鲸鱼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强大的反捕鲸运动。 又如,1968年,通过“阿波罗8号”飞船的镜头,地球人第一次通过直播看到了自己的星球。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星球很小而且与世隔绝。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地方,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它的珍贵是独一无二的。”
做自然科普已经第十一年了,很多人仍然问张晨亮:知道你的花鸟鱼虫的名字有什么用?
“其实我对这种问题很恼火。但既然大家都在问,与其去对抗,不如想想如何让这些知识变得有用。” 张辰良给自己想了一个解释,听起来很平淡:他看到你说完了,你可以在酒桌上和朋友们吹嘘你教的知识。 这没用吗?
如果我们现在拍香格里拉、墨脱、新疆花海,观众看完这些片子后,可能会产生自驾去那里旅游的愿望。 当他们真正到了现场,看到这些物种的时候,就会感觉特别亲切:嘿嘿,这不是小亮说的吗!
“他们不只是看看就过去,甚至可能会喊,哎呀,停车,我下去拍张照片!” 张晨亮说,这就是科普的运用,“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排版:孙Sunboy/审稿:冉宁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