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学术明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柳青、项彪、薛兆丰、罗翔、戴建业、戴锦华、沉逸飞……
2020年6月,哔哩哔哩顺势建立知识区,积极邀请各类学者入驻,沉逸飞、戴建业、戴锦华均开通了公众号。 知识区也成为2020年B站增长最快的版块之一。
2021年9月,快手还推出了常识类谈话节目,邀请沉逸飞、韩秀云、付鹏等嘉宾亮相。 节目的口号是“吃了你就懂了”。 泛知识已成为增长最快的内容类别之一。 《2021快手内容生态半年报》显示,平台60秒以上视频增长前五的类别分别是:法律、科普、金融、资讯、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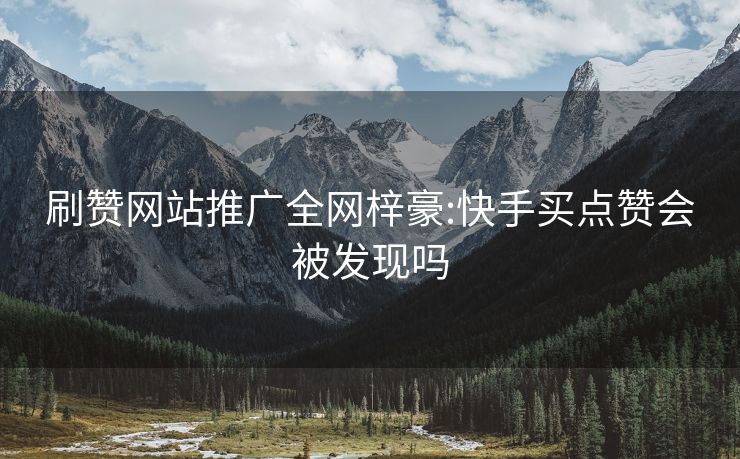
显然,如今的学术偶像与2000年后“百人论坛”式的学术明星有很大不同。于丹、易中天等人讨论的大多是国学、历史,甚至是心灵鸡汤,关系不大。与现实。 然而,当今大多数学者需要直接回应现实,社会科学在他们中尤其受欢迎。
原因之一是社会转型下,人们需要通过这些学科来认识世界、解答困惑。
然而,当社会科学知识普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新的现象——知识鸡汤。
为什么现在流行知识鸡汤?
流行叙事是通过社会科学建立的。
过去,鸡汤宣扬的是正能量,“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现在社会学强调个人受制于整个社会结构。 当然社会学教的是事实,但对于每一个运用这些社会学的网友来说,知识往往就变成了另一种鸡汤。
以贫困为例,社会学知识会告诉人们,穷人不应该被污名化,因为在没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情况下,一个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转型,所以贫困是体制问题。
在当前环境下,这种说辞自然有吸引力,因为它通过理论解释了年轻人感受到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在认识到社会层面的原因之后,一个普通人有机会通过合理化自己的处境,进一步将自己“糟糕的生活”的责任指向一个抽象而模糊的庞然大物——社会。
而且,指责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比谈论身边具体琐碎的事情更有成就感。
有没有发现,现在社交网络上,似乎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声音。 当面对一种现象时,集体下意识地运用相同的理论来解释它。 比如“异化、规训、消费社会”等等,这些词大多都是在谈论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对象。
它们在公共讨论中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一种常见用法:
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你说你被劳动、被老板PUA“疏远”;
出于尊重而遵守社会规则,就是“受纪律”;
如果你只是买东西,你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
每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事件之外的所有人都必须集体反思,因为俗话说“平庸之恶”,“没有雪花是无辜的”;
有内部竞争,就是“内卷化”;
追星时点几个赞就是“数据工作者”;
打开抖音、快手“娱乐死”;
男性夸大异性美丽是“男性凝视”和“性别霸权”;
有的人扎堆,扎堆,叫“乌合之众”;有的人扎堆,聚在一起,叫“乌合之众”;
为弱势群体说话是“政治正确”;
每个动作都很快被归类,归类之后就可以直接批评,甚至不批评。
一方面,这种知识当然是普通人试图保持自我一致性的工具——“资本的压迫和阶级的固化都是制度的错”。 不管怎样,从目前工作上的不如意到生活上的一切,都可以用它们来解释。 出路的问题。 它的确定性非常有吸引力。 但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便利的坏处在于,它会形成一个舒适的、愤世嫉俗的闭环,“我是一根韭菜,这个世界很糟糕,年轻人除了躺着没有出路。” ”
对于现实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却也是自洽的逃避。
知识鸡汤带来什么?
这些词语是从学术界引入日常生活的。 它们的流行或许并不反映学术理论的繁荣,而是反映理解的模式。
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大多数知识在经过历史检验后都会不断变化,也会受到权力、通讯等外部力量的干扰。 然而,很多人仍然相信它,并将其视为“教科书”。 知识被视为一个结论、一个事实,它是结论性的,形成某种“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东西。 人们认为理论是完美的并且100%符合现实。
社会学家徐弼表示,教科书是一项利弊参半的发明。 从现在起,所有学生都必须使用同一本教科书。 教科书是可靠知识的基准。 换句话说,知识有一个“标准答案”。
当代中小学生的这种思维,当他们进化成成年人时,就是对专家学者的信任(我很同意):他们相信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答案”。
因此,我们更容易找到符合理论的现实,并让现实进一步“支持”理论,变成循环论证:“因为符合理论,所以合理”。 从那以后,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理论。 当你看到巨魔在网络上横行时,因为他们已经加载了“乌合之众/思想自由市场/沉默螺旋/大众智慧”等理论说辞,人们会同意这种行为很正常,“流氓,乌合之众”。
心理学上有一个认知偏差的概念叫“证实偏差”,指的是无论事实如何,人们都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偏见和猜想,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劫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来证实我们所相信的理论——这样做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因为我们想如此相信。
知识原本是“我”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却取代了现实本身,成为了更真实的东西。 而这些个体的细微差别在这些抽象的概括中被忽略了。
这就是为什么关心社会的人倾向于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尽管从许多指标来看世界正在变得更好,但他们不忍心相信这一点。 社交媒体对“不良信息”的偏爱也趁机传播悲观情绪。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单一的解释就能让世界显得更加有序、可控。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省去“一次讨论一件事”的麻烦,用一个理由解释一切(例如“系统的错”)。 但如果对解释的要求太高,经过层层抽象后,很容易与现实脱钩,变成抽象的、模糊的、包容性的“概念”。
例如,现在很多人热衷于将政治倡导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而不是现实的制度安排或技术手段。 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句话是,民族主义意味着仇恨和排外,全球主义意味着开放。
然而,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提出快手买点赞会被发现吗,友谊是许多公共政策的前提,全球主义实际上逃避了社会责任。 此外,保罗·科利尔警告说:意识形态提供了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的诱人组合,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
从知识鸡汤到知识愚蠢
测试一个概念的一种方法是看看它从抽象到抽象的具体程度。 “价值太高”的说法与现实生活没有办法对应。
例如,有一天,一名男子出现在街上裸奔。 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谈论衣着自由、羞耻的原因、男性的情欲以及人类贞操的历史。 当你问这一切的具体问题时,对方除了重复整个理论之外,基本上没有办法回应。 这类言论通常从一个特定的事件开始,最终蔓延到整个群体,甚至整个人类。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区分了“对全人类的爱”和“对一个人的爱”。 他认为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遥远的、非个人的爱。 他认为这种普遍的爱是廉价的,因为它不仅简单,不涉及任何牺牲的风险,而且还能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心。
换句话说,当只谈论概念时,知识很容易变成语言游戏。 谈论理论的人可能并不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而是满足于自己的渊博知识,甚至慈善事业。
近年来许多知识分子被“抛弃”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发现拥有知识似乎并不能让人成为更好的人,尤其是当知识看起来是政治正确的时候。 道德知识并不能直接导致“这个人有道德”的结果。
“周宣仪事件”之后,很多人开始怀疑“女权男”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 但归根结底,一个人,无论性别如何,都可能具有“女权”性格,熟悉波伏娃和巴特勒,被认定为女性,但同时在陌生女性受到威胁时保持沉默。 叹了口气,我拍了张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同时感慨:环境对女孩子来说真的很糟糕)。 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在私下物化女性,用黄色笑话吹嘘自己的性经历和能力,把她们当作性猎物。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只是表明你有主见和关心的一个道具。
而打着“道德”、“正确”旗号的知识,可以使自己合理化,进而攻击他人。
在《维特根斯坦传》中,有一个故事描述了这个坏习惯:
“他们经过一个报摊快手买点赞会被发现吗,上面有一个标语,上面写着德国政府指责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表示,如果这是真的,他不会感到惊讶。马尔科姆表示反对。他说,这种行为与英国的“民族性格不相容”。 ”维特根斯坦对这种“粗鲁”的论点做出了愤怒的回应:
如果学习哲学对你来说意味着让你能够合理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不能提高你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那么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呢?不会让你比记者(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词的人)更加谨慎地使用某些危险词。 ”
结尾
内容行业报道第一新媒体
刺猬公社是一个专注于内容产业的垂直资讯平台。 其重点领域包括互联网资讯、社交、长视频、短视频、音频、影视娱乐、内容创业、二次元等。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