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曾小濂美术馆在1999年昆明世博会旧址开馆。
曾孝濂今年82岁,被誉为“中国第一植物画家”。
1939年出生于云南维新,一生在云南,只做一件事:画自然界万物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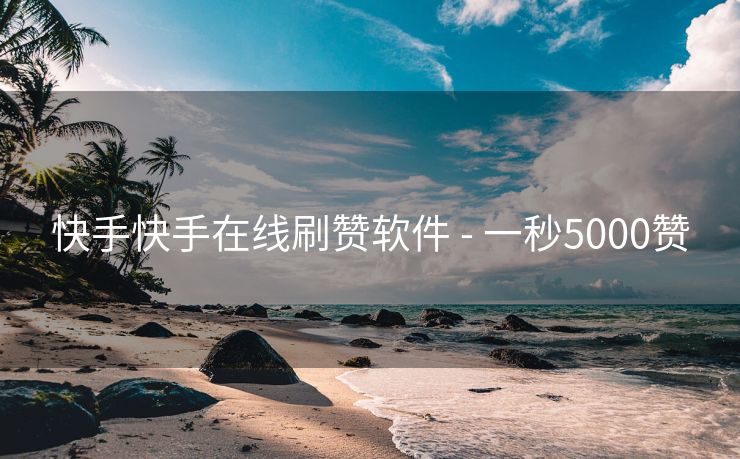
19岁加入昆明植物研究所绘图团队,用40年时间为中国数千种植物制作科学绘图,被《中国论坛》和《云南论坛》收录。
存有黑白水墨线条图2000余幅,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退休二十多年来,他实现了多年积累的生物绘画题材,画花鸟,“是对自然的准确描绘,是对美和生命的崇高礼赞”。
曾孝廉美术馆于2021年12月刚刚开幕
花园里的素描
2019年,他患上肺癌,手术后失去了两片肺叶,但他仍然没有停止绘画。
现在他和妻子搬回了昆明植物研究所,住在只有30平方米左右的专家公寓里,物欲极低,朴素而自由。
近两年,曾孝濂的作品陆续出版,并在昆明举办了两次个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了他。
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自发在网上组队,交流学习他的植物画一秒5000赞,但他不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红了。
令人惊叹的是,曾孝濂每天画画9个多小时,与时间赛跑。 他还有下一个“三年计划”,要重返版纳雨林,画100幅画……
曾孝濂1982年至2021年绘画作品
“太薄!”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曾孝濂的画时,我们手里拿着画册,瞪大了眼睛。
到了博物馆展厅,大家都想把头靠在玻璃框上:
花蕊可一一数得出来,每片叶子的脉络都有层次,鸟的绒毛和影子都分明……
如果你看得更远,你会看到纸上盛开的花朵;
下一秒,鸟儿振翅飞翔——这样一幅充满生机、专注、极力歌颂美与自然的画作,实属罕见。
这是一生画植物画的云南人曾孝濂,82岁时创作的作品。 它被称为生物绘画,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
紫薇
地金莲
黄颈鹛
退休前,曾孝濂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家、工程师。 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该研究所,并“选择了一生要做的一件事”——画植物。
最大的成就是参加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 这部宏伟的杰作附有丰富的插图。 全书共80卷、126卷,逾5000万字。 它记录了我国3万多种植物,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
该项目于1959年启动,2004年发表,历时40多年,涉及300多名植物学家。
全国负责这些插画的插画师总数为164人,目前其中一半以上已经去世。
泡桐的科学插图,整体和部分,绘制于 1976 年
云南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聚集地和物种基因库。
退休后,创作更加自由的曾孝濂在云南画了数百种花鸟。
他所描绘的许多物品被列为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珍稀动植物。
毫不夸张地说,它既是“对自然的准确描绘,也是对美和生命的崇高致敬”。
杜鹃红山茶花 2018
云南细菌2020
他设计的邮票在私人收藏中也拥有众多粉丝。
2008年,一套6张“中国鸟”门票荣获世界大奖。
《中国鸟》2008-4T荣获第十三届政府间印商会议最佳连续邮票奖。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次获此殊荣。
2019年,80岁的曾孝濂闭门半年,创作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画作——《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描绘了水稻、大豆、桑树、银杏、苞叶等37种中国本土植物,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展出,令世界惊叹。
与这幅巨画展出的同时,昆明当代美术馆举办了曾孝濂在家乡的首次个展。
但展览开幕时,曾孝濂在例行体检时被诊断出患有肿瘤。 他在北京接受手术和休养,但遗憾错过了。
2019年画《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2020年至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首次在中国昆明举行。
以此为契机,99昆明世博园(1999年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公园)旧址开始改造。
昆明当代艺术馆馆长聂荣庆想到曾小濂先生,进行了三个月的极限规划和改造,将公园内的巴基斯坦博物馆旧址改造成曾小濂的个人艺术博物馆。
建筑部分由聂观的老朋友建筑师杨雄负责。 他用玻璃罩轻轻地保护了原址上现存的废墟。
曾孝濂美术馆
建筑设计:竹翔建筑摄影:王策
当你走进这个小型艺术博物馆时,一切都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画作和鲜花。
在曾孝濂的新花鸟画旁边,几步之遥,你就会被各种热带和温带植物所包围。
采访当天上午9点刚过,曾孝濂准时出现在美术馆。
一到就询问温室里的植物,温度够不够高,多久喷水一次……
冬日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坐在他最喜欢的热带植物旁,开始向这位热爱大自然的爷爷询问他的故事。
01
在植物研究所从零开始
“三点一线”40年
曾孝濂,1939年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
19岁那年,曾孝濂高中毕业,但没有上大学。 他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当学徒,兼职。
1959年,《中国植物志》的编撰任务下放到全国各单位。
曾孝濂小时候喜欢涂鸦,所以他从一名见习绘图员开始,从零开始学习画植物。
“中国论坛”的意义在于对分布在中国大地上的植物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
植物学家负责用文字描述植物的特征,找到它们在植物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并定位它们的生物学关系。
绘图团队需要与各科属的植物学家合作,用画笔直观地表达植物各部分的形象特征。
这种植物科学插图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后来成为西方植物学界的传统。
在我国,它是由20世纪20年代“生物绘画大师”冯成儒首先引进的,并走出了中国第二代科学画家。
然而,当时曾孝濂所在的昆明画院被认为是“边塞画院”,没有一个懂技法的画家去过那里。
“这就是自学啊!” 曾孝濂和我们一起回忆了往事。 “就是研究所里的‘三点一线’、植物标本室、植物园、图书馆。”
《植物群》中的绘画最初主要以蜡叶标本为基础。
之后,我开始在植物园写生,近距离、多角度观察植物生动的姿态。
最后,根据样本的结构起草组合物。
晚上,曾孝濂去图书馆抄书学习。
欧洲权威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有四五个大书架,是他最好的“老师”。
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咨询植物学家。
植物学家可能一生只研究一两个科和属,但画家却在一起工作。
当我把一个科属的植物画到另一个科属的植物后一秒5000赞,我必须从头开始记住它们的特征,并向另一位植物学家寻求建议。
给曾晓莲印象最深、印象最深的就是唇形科植物。 光是画这幅画,她就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为了了解结构,我不仅画了草图,还在植物园里解剖了山上的许多野生植物。
解决了长久以来唇形科植物的难题后,曾孝濂觉得自己基本了解了生物绘画的要求、方法、规则,并开始了创作。
坐上替补席后,他开始喜欢上这份工作,“既然喜欢,那就做好”。
为了画得准确、生动,他总是坐着不动。
20世纪70年代,研究所里彩色相机还很稀缺,他就交出了一套完整的昆明市花茶花彩色图集。
被誉为“最美花”的淀山茶是怎样画出来的?
他回忆道:
“天快亮的时候,我去植物园摘了一朵山茶花,跑回办公室把它装进瓶子里。
赶紧去吃早饭,吃点东西再回来画画。
我画到十二点半才吃午饭。 整整五个小时,我没有喝水,也没有上厕所。 我全神贯注。 ”
“一朵花从植物园采摘下来的那一刻,它就会慢慢地绽放,如果你画得慢,你就会找不到关系,会很紧张。
而且当你画这个的时候,你不能构图然后画出来。 你必须从离你最近的花瓣开始,逐瓣地画它。
当它结束时,我会浑身发抖。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热量消失了。 ”
他画半天、一天,如行云流水,一画就是几十年。
如果你随便打开《中国植物志》,你确实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插图是曾孝濂的作品。 都是以死去的标本为基础的,他的植物确实更“活”。
除《中国植物志》外,曾孝濂在植物所工作的四十年间,还参与了《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50余部植物专着的科学绘图工作。 共收集到2000多件。
中国植物科学绘画学术交流会代表合影
昆明 1983
02
从植物到自然界的万物
1997年退休后,曾孝濂开始选择自己的题材。
第一幅是我心心念念已久的《百鸟图》。
画作不仅“真实”,鸟儿栖息的生态环境、一枝一灌木也栩栩如生。
红脚鹬,1995年绘制
云南省滇南地区独有的冬季候鸟
黄胸织雀,画于 1994 年
善于编织巢穴,是“鸟中建筑师”
为什么要在这些环境中画鸟?
这与他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丛林五年》密不可分。
当时,昆明植物研究所承担了两项国家专项任务:
一是代号523,是在热带丛林寻找治疗恶性疟的中草药(多年后被公认为有效药物的青蒿素,就是当年发现的);
一是制作“热点地区野菜地图”和“热点地区军马饲料”,了解丛林中哪些植物可以食用,以及军马人员被困时如何自救。
曾孝濂这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南边疆、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度过。
他没有向我们提及当时的条件有多困难,只是拿出了一张罕见的照片:
他独自坐在溪边写生,仿佛完全融入了大自然。
曾孝濂说:“那五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了解了自然。”
他发现“山中出俊鸟”这句话是真的。 “早上,黎明前,鸟儿开始齐声鸣叫。”
短短两年时间,他画了近百幅鸟类画作,大部分是来自云南的鸟类,“几乎是他在丛林中见过的所有鸟类”。 其中一幅作品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也是和画植物一样的“笨技”。 他在北京动物园生活了半年多。 他每天去鸟园观察鸟类的姿势、画素描、拍照,还去昆明动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详细记录各种鸟类的特征。 对于形态特征,请咨询鸟类专家...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