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LatePost(ID:postlate)
作者:朱英丽、朱丽坤、姚银宓
责任编辑:姚银宓

图片来源:TuChong Creative
离开大工厂体制去创业
第一步很难
曾任蚂蚁金服、字节跳动电商工程师的陈希(化名)决定彻底脱离大型互联网公司,自己创业。他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但真正执行起来,却跌了一步。
去年9月,他在各大互联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广告,但等了一周,邮箱却空空如也。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便在平台上注册了会员,用搜索功能留言,但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陈曦突然意识到,在Boss直聘上招厨师是不可能了。
陈曦的创业方向是潮汕菜预制菜,为了找到能帮上忙的厨师,他只能到当地去找厨师,到了镇上才发现,大厨们都通过人才引进机构转行了。
陈希在大公司做过“从0到1”的事情,自以为掌握了创业的方法。2018年,阿里巴巴在集团层面启动新项目,他从技术转做运营,从运营转做项目经理,建团队、找资源,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内部创业者。
直到离开互联网大公司体系,自己创业,他才真正明白那个“0”意味着什么。
陈曦的第一个快餐产品是“牛肉丸米粉”,他原本以为产业链成熟,工厂会很乐意参与进来,但工厂的管理者看不起他的小公司——“潮汕以外的食物还能叫潮汕菜吗?”跑了20多个城市后,他终于在广东河源市找到了一家工厂。
在和工厂打磨产品的几个月里,陈希把自己140平米的豪华装修房借给了朋友。以前他出门都能住五星级酒店快手买站一块钱1000,现在只能住县城里几十块钱一晚的宾馆。他想,我得能吃苦,创业就是要吃苦。朋友比他更有觉悟:“你又不是睡在天桥上,怎么会觉得苦呢?”
他曾吃过以前以为吃不下的苦头,但成功并未到来。要做无防腐剂常温预制菜,需要经过121摄氏度的高温杀菌,但牛肉丸在高温下直接爆裂,再也没有了潮汕肉丸的嚼劲,而是变得软塌塌的。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品类,转而做猪蹄饭。
在互联网公司,一个功能一两周就能完成,而在传统行业,所需时间“大概是十几倍、几十倍”。工人们需要检查、排班、加班,一两个月才能出结果。经过一系列的失败和重新开始,正式创业四个月后,陈曦终于在河源市连平县的一家工厂里做出了潮汕常温预制菜。
前快手员工王可乐也有类似经历。他是快手资深员工,员工号在600强,负责运营和营销。他在那里工作了6年,见证了公司估值增长数百倍,也看到了大规模扩张过程中管理混乱、内容贫乏、内部腐败等问题。“无意义感”不断增强,在80%的业务被微博的职业经理人拿走后,他闲置了半年。
2021年9月最后一天,王克乐赎回了自己的第一笔期权,拿到几百万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精酿啤酒“人间九华”的创业中,产品研发费劲是意料之中的事,最想不到的是,他最擅长的渠道营销却遭遇了极大挫折。
在互联网公司积累的经验和见证的变化让王克乐坚信,一个产品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品质是关键,而营销则是成功的关键。
他非常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工具,将新品牌刻进消费者心智。2016年加入快手时,全国知名短视频网红屈指可数,借助平台流量资源,他帮助不少当下头部网红成功“一路顺风”。2020年,哔哩哔哩营销视频《后浪》爆红后,他又花了7天策划快手宣传视频《看见》,邀请快手用户“Oli Gei”大叔演讲,成为当年的热门营销案例。
没想到,当他开始做精酿啤酒时,却被现实打了一巴掌。产品达到量产标准后,他想给罐子喷漆——毕竟外观也是品牌的一部分——但找到工厂后,他们说只接30万瓶以上的订单。达到这个数量需要时间,所以他只能在罐子外面贴上一圈贴纸。
朋友们刚知道他做新消费品生意时,纷纷夸赞:“可乐,贴个标签,放到直播间里,一年就能赚5个亿到10个亿。”之前的工作让他认识了很多网红和短视频达人,关系都不错。不过,因为抖音酒水资质比较高,需要在淘宝、京东达到一定的销量,他连开抖音店的资质都没有,连共享单车都用不了。
真正进入实体经济后,陈曦更加深刻感受到其中的艰辛和负担。实体经济需要投入买机器、建工厂,还要承担卖不出去货的风险。王克乐也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不太依赖运气的行业。“对于消费品,你要老老实实了解每一种原材料,还要精打细算每一个供应商的每一分钱。”
陈希做出产品后第二个月,疫情再次来袭。订单量下降、物流停摆、现金流没有了,他十多人的团队不得不裁掉一半,投入的一百多万可能打水漂。辞职创业前,新消费浪潮传来的信息是:“所有消费产品都值得再做一次”;而现在,“不管你做得有多好,投资人都不看这个领域了。”
这就是独立的代价。王克乐感叹,以前在大公司,自己算是节俭的领导,一年几百万元的预算,“花了就意味着完成了工作”。现在的他非常抠门,买几万元流量都要精打细算投入产出比。最近,一罐产品送到用户手上时被挤压变形,他下定决心全部转投京东物流,每单成本增加16元,让他很心疼。
今年4月,第一瓶啤酒成功装瓶后,王克乐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前互联网员工
使用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东西来做事
创业之初,王克乐就已经思考好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并融入到员工的行为准则中,在大公司观察和学习的经验,成为了他现在的创业方法论。
在研发第一款啤酒口味时,他从淘宝、京东畅销产品中提取配方参数,并请农大的老师反复实验、调整,找到最适合大众的精酿啤酒口味;用思维导图分解用户喝啤酒的场景和原因;通过私域跑核心用户模型;用小流量测试的方式,测试不同版本的营销创意效果。
陈曦和王克乐的团队规模都很小,每人不到10人,但都用OKR来管理员工,也引入了互联网测试、快速迭代的思想。
陈曦用灰度测试、整体优化的方式打磨产品,也用敏捷迭代的方式根据已上市产品的反馈快速调整。公司的口号是:用科技改造传统食品,倡导美食。“改造”就是“复制新鲜”。
王可乐熟悉不同平台的流量特点:抖音是泉源,流量呈漩涡状,只要花钱,可以瞬间聚集大量流量;B站因为有游戏厂商竞价,性价比较低;小红书是流量洼地,粉丝少的网红也能获得流量。
他还没赚到钱,没钱抓流量这头“大象”,把目光瞄准了“蚁群”——主要在小红书。40箱啤酒送给一位只有2万粉丝的博主,直播时同时在线人数不足40人,打开链接后瞬间卖出30箱。虽然单次销量有限,但这个过程“就像端着盆子去收集分布在不同荷叶上的小雨滴”,辛苦,但有效。
在选择包装设计时,王克乐运用了互联网内容营销的思路,第一款啤酒包装的颜色是绿色,在营销文案中,他称之为“宽恕绿”——象征意义大于设计意义,幽默又自嘲,迎合社交网络上的某些情绪,能激发更多衍生讨论,带来更多传播。
这些曾在不同公司工作、在不同城市生活过的互联网背景的创业者一致认为,“好的产品是会被用户看到的。”正如王克乐所说,“移动互联网第一点是产品体验,第二点是社交货币。”
并不是所有离开的互联网从业者都有机会像陈曦、王克乐一样创业,他们的资本是行业和时代赋予的,他们都是85后,加入互联网公司时都有机会抓住最后一波红利。
2013年,陈希从一所普通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毕业。他这样描述当时年轻人对互联网的向往:“能进腾讯这样的公司,你会很自豪。”他毕业离开学校时,是学校里薪水最高的人。两年后,当他离开腾讯时,薪水是刚进公司时的两倍。
陈希加入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证券公司的互联网部门。那是2015年,阿里巴巴刚刚创造了当时全球历史上最大的IPO神话,“传统”公司也在加速互联网化。在这家证券公司,他的同事们来自雅虎、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
他第二次辞职前让我猜一下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根据我之前的了解,我给出了一个数字:3万?
“搞笑啊,六万。”陈曦说,“你信吗?”
他把积蓄和工资都投入股市,还买了一些虚拟货币,赶上了大牛市,在证券公司工作期间,他攒下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那时刚毕业三年。
在互联网公司的这些年,陈希走访了几十个国家,并确认自己“一生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和自由的最大化”,而是“我这一生能不能做一些有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阿里巴巴的四年时间里,陈希在四大事业群任职,从前端工程师成长为全栈工程师。通过内部创业项目的经历,他培养了独立创业的能力。包括理财收入,到毕业后的第六年,不到30岁的他,资产已经突破1000万。这些资产和经验,是陈希创业信心的来源。
离职员工重返现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顺利的互联网从业者的故事,还有更多的人,最近都主动或者被动的离开了互联网,没有太多的选择。
1996年出生的冯淼一毕业就加入了拼多多,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工资待遇还行,包吃包住,是2019年为数不多能加入的快速成长型公司之一。但没过多久,他对互联网的幻想就破灭了。
公司要求所有新员工都要在客服岗位轮岗三个月。身为HR,冯淼给自己洗脑,告诉他们“这个岗位很值钱,虽然是客服,但也是运营、产品,学到的东西都一样。”但他没法用这种方式说服自己的朋友和校友。按照部门规定,如果有人向他透露离职想法,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否则就是失职。
冯淼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却被高层强行调到快团。领导说以后要参与运营、产品、数据,但实际上他只是拿着两三千人的名单打电话,直到有人接电话或者愿意加微信。他看到同组一个有四五年工作经验的主管被高薪挖走,还天天打电话,“感觉自己忙不过来。”
离开拼多多之后,冯淼决定不加入大型互联网公司,他回老家休息了两个月,有了父母的积蓄做后盾,他不再觉得需要赚那么多钱,五六千块钱足够日常开销了。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想过考研,也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但他所应聘的职位招聘比例高达1:500,再加上准备不充分,自然落选了。
2021年6月,休整近一年的冯淼被高中好友邀请,一起创业,做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冯淼花了三个月时间与一所国际学校签订了宣讲协议、准备了项目书、思考合伙人入股事宜。7月底,“双减”政策出台,疫情防控不能进校园,短期创业被搁置。没路可走的冯淼在一家电商公司找到了一份运营工作。2022年初,公司搬迁到杭州,他又失业了。
他知道自己的简历上漏洞百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晋升希望不大,失去的两年就像是被挖了一个洞。今年4月,搁置的教育培训项目又被提起,一位朋友在加拿大已经把项目推进正轨,也有一定的现金流,希望在国内市场有所突破。
线下教培受到外界制约,冯淼自知无能为力。他一边答应朋友,一边在心里设定时间节点:一个是暑假,一个是开学。“如果两个都做不好,就找个五六千块的工作吧。”
2021年8月,同样受到“双减”政策的影响,字节跳动大力教育原员工戴菁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在线教育视频总监生涯。
失业第一天,她很激动,因为“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第15天,她去一家公司面试,她跟面试官讨论如何做内容,但面试官更关心“这个东西怎么卖”,而她对销售、运营、推广一无所知。
第83天,在又两次面试失败后,戴菁终于接受年龄确实是一道坎。“没有公司会请一个38岁的人做她没做过的事”,她说。她曾经打破过互联网行业的“35岁魔咒”。加入字节跳动时,她刚过完38岁生日。当时的朋友惊呼,“这么大年纪能进公司,太可怕了!”入职前,戴菁手下有十几个,但到了字节跳动,她又变成了草根。她没太在意,因为那时她真心相信字节跳动的教育业务会“大”。
2021年1月底,她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利用上一份工作那几天的年假搬家。HR催她:“你就是我年前的目标,赶紧来。”2021年3月,达利教育加速扩张,宣布“未来4个月招1万人”。
戴静对教育有情怀,是典型的字节跳动好员工:她会抽出额外的时间教刚毕业的同事怎么写故事;她会花至少半天时间准备小组分享,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的经验;周末,她还会主动“监课”,关注观看直播的孩子的表情和动作,观察他们是否被自己写的段子逗乐了,是否能听懂知识点——这是不算在 OKR 里的工作。
第107天,“失业日记”变身“创业日记”,戴菁在北京做起了自己的花艺生意。她想自己打理一门小生意,就像她去日本旅游时看到的一样——拉面店老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在乡下开个小店,不用在大城市里争抢大公司的职位,过着体面的生活。
小本经营也需要考虑如何线上引流。她对抖音卖花抖音的花招感到很反感,虽然前同事提醒她多发朋友圈推广帖,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脸皮不够厚”。最终,戴静选择了最原始的获客方式——摆地摊。她还给自己设计了“全国十城摆地摊计划”。结果,全国各地的摊位都因疫情而泡汤。第三次在北京摆地摊时,她的车被城管没收,还被罚款100元。
疫情的反复爆发,对中小型实体店的冲击最大。2022年6月,一位学插花的朋友因封城无法离开小区,戴静就帮她把朋友的花店关了。她不再指望立刻开实体店,而是在家里腾出一间房间做花房,只接受网络订单和社区团购订单。
卖花的艰辛是具象的。有一次,她接到一个活动业务的临时订单,等不及云南的鲜花。她早上六点出门,天刚蒙蒙亮就坐地铁从西三环到了东北五环外的花市。回到地铁站时,正是上下班高峰。戴静挤了七束花进去。2022年情人节,她连续包了40束花。骑共享单车回家时,她觉得车把歪了。她换了一辆,还是歪。“完了!不是车的错!”戴静边说边笑:因为一直在用左手干活,“感觉自己‘瘫痪’了。”
互联网不是一切
如果公司能成功上市,陈曦又将经历一次“财富大增”。突然中止上市,他的期权价值缩水了一半,兑现的时间也遥遥无期。“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开始想离开。第七年,他观察到,互联网曾经通过高薪吸引“社会顶层的精英”,但后来“注水比较高,钱投了,但人却没有以前那么精英了”。
王可乐离开快手时,手里还有四分之三的期权可以赎回,按现在的价格,价值超过一千万元。对于离开,他想得很清楚,“真正想走的人,门关得很轻。”
离职前,他曾撰写了一篇千字文章,劝告管理层“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虽然我要离开了,但我希望大家能坚守快手最初的朴素愿望,做好产品。”他说。
发表文章后,他便扬长而去,并迅速搬出了北京。
互联网行业曾经享有所有人的赞誉,先进、扁平、高效、福利好,是过去20年诞生最多大公司和巨头的行业。从咨询业转行过来的杨晓(化名)被蓬勃发展的互联网行业所吸引,加入腾讯不到两年,又重回咨询公司。在腾讯,他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
第一,抢着向上级汇报:事情做了不汇报,相当于没做;事情做了,另一个团队汇报,那是另一个团队的成果;事情没做好,汇报好了,成果还不错。员工们编造各种数字来应对KPI。一个项目中,不同部门会把相同的绩效收入算作自己的,看似达到了目标,但因为重复统计,多数部门的营收和增长指标难以达成。业务频繁变动,缺乏反馈也让他很失望。加班三个月才交出成果,老板突然说,换方向。
杨晓离开互联网公司,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继续留在大型互联网公司,升职机会会少一些。回到年年涨薪、几年升职的咨询行业,他的确定性更强,觉得自己做的是更踏实的事情。在互联网公司业务和团队都在萎缩的今年,杨晓更庆幸自己的选择——他原来的部门是腾讯裁员的重灾区之一。
离开互联网之后,看到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的宏观运行逻辑,前员工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互联网虽然富有创造力、影响力巨大,但它并不是一切。
前小米员工任心怡,大学毕业时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去北京,只应聘互联网产品经理岗位。即使简历没被录用,她也会直接去“抢面试”——那时候,大公司都会开辟专门的面试通道,欢迎敢于拼搏的年轻人。怀着“不面试我就损失一个人才”的想法,只要看到机会的缝隙,她就会满怀信心地冲上去打开。
2016年,任馨懿转岗加入小爱同学创业团队时,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她,要从零开始学习AI和硬件。总经理、产品总监跟她坐在不到15平米的办公室里,什么任务都“点头示意”。她负责设计了五六个重要的基础功能,其中一半在上线后成为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10大功能。2018年7月,小爱同学上市仅一年零四个月,月活跃设备超过3000万台,累计唤醒超过50亿次。那是她加入互联网公司后最开心、最充实的时光。
产品走出了超出预期的第一步之后,才会更快的进入第二阶段——商业化。单个产品开发的原则无法左右公司的策略。2019年,基础功能界面旁边开始出现各类广告主的品牌图标,广告内容也被植入其中,比如你对音箱说“带我去兜风”,它就会推荐你买一辆福特 Kuga。
2020年,任心怡离开小米,因为AI领域已经不吃香了。她回到家乡杭州,那里只有阿里巴巴和“其他公司”。她选择阿里巴巴“早已过了最佳入职时机”。杭州字节跳动、快手挖走了她,但同一职位的薪资只有北京的80%。她感叹,如果自己早出生几年,就能得到“更符合自己能力和抱负的工作”。
平心而论,任心怡是幸运的,2018年她开始招人的时候,简历上90%都是研究生学历,像她这样的211本科生,很难在大公司获得好机会。
2021年,她选择做全职保险经纪人。保险行业对她来说,是当下最理想的职业:薪资不限,“自己当老板”,满足自己的职业抱负。她还发现,最近不少30多岁的互联网人都在寻找新出路,她要“提前占个位子”。
保险行业让她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也让她重新认识了大公司所创造的“常态”。
她曾与一位医生客户聊天,问他你们这个行业如何才能年入百万。医生说,年入百万的都在省级三甲医院的外科,博士毕业后至少要干10年——从互联网的角度衡量,ROI很低。以前互联网人跳槽可以获得加薪和期权,但有些医生跳槽后要在新科室从基层重新做起,要半年到一年才能达到正常收入。
互联网人自称是“打工者”、“社会动物”快手买站一块钱1000,但一位医生曾谈及半夜被电话吵醒、被无理患者家属责骂、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家人等内心的惶恐。在她看来,互联网人在工作时无需面对生老病死等负面情绪,已经是“安逸且幸运”了。
她也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像互联网这样急迫。当她还在互联网行业时,身边的年轻人很少在一家公司待超过5年。但她的一个投资行业客户,7年都没有换过工作,对自己选择的细分领域很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长期坚持下去。年龄不是问题。他听心怡说,以前9点、10点下班很正常,很震惊地说:“我还以为你说加班到7点呢。”
在北京时,任心怡和丈夫的朋友们都是来自服务千万级用户的互联网巨头的年轻人,他们有很高的自我认知度,认为“互联网很强大,我们做的是中国最有创新力的东西,创造的服务和价值最多”。每次聚会,她都会和AI同事们聊,要做什么新的硬件产品,如何实现车载场景。互联网的话语体系无形中把她和“外来者”区分开来。
转行越久,她就越喜欢现在的工作生活。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拓宽了她的人生观。“这让我这个曾经很绝对的人变得不一样了,”她说。
现在,她看到了更广阔世界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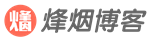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