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信息中介的平台往往对内容生产者的这种“玩弄算法”的行为持贬低和反感的态度(Cotter,2019),内容生产者被动接受平台的内容审查,构成“算法游戏”的实践。平台一方面强调“技术中立”,回避责任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进行内容审查,并以此确立自身的合法性。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谷歌、Facebook、Instagram等平台通过建立特定的话语框架界定内容生产领域的道德边界,确立了平台家长制的权威(Petre,Duffy & Hund,2019)。
在中国语境中,“算法博弈”与平台家长制的动态同样可见一斑。基于此背景,有必要关注文化生产者、平台与算法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延续Caitlin Petre等(2019)的思路,本文进一步推进了平台家长制的话语建构与运作机制的考察。在中国语境中,科技平台如何重塑内容生产领域的面貌?平台对内容生产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信息中介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媒体内容生态的治理责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相关媒体话语,探讨“算法博弈”的界定与内容审核构成了怎样的话语实践,以及这种话语将对当代文化生产与平台权力动态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

“算法游戏”与平台家长制的兴起
1. 从“玩算法”到“算法游戏”
在算法、用户与平台的互动过程中,平台和算法并不会单方面决定用户的行为。用户会以各种方式将算法嵌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反抗、颠覆和改写算法的意图(Kitchin,2017)。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玩弄算法”,即用户基于对算法系统的了解而采取行动,以影响某种结果的输出(Cotter,2019;Ziewitz,2019)。长期以来,信息技术平台将用户“玩弄算法”的威胁作为隐藏系统的理由(Pasquale,2015:94),例如刷好评、搜索引擎优化、诱导分享等。由于这种做法被视为“作弊”,可能会干扰算法的运行,从而破坏系统运行结果的完整性。 “玩弄算法”的话语建构为平台所有者提供了合法理由,使他们可以对算法保密以保持竞争优势,避免自我审查,同时又有权审查“玩家”(Pasquale,2015:204)。
然而,“玩转算法”将主体限定在内容生产者身上,而忽略了其他参与主体,如算法、平台所有者和其他参与者。因此,“玩转算法”的概念发生了关系转移,参照对象也从单一主体转变为多个行为主体的集合,意在探索不同主体之间围绕算法可见性的相互依赖关系(Cotter,2019)。“玩转算法游戏”构成了平台、算法和用户之间互动的关键机制,算法可见性是奖励,通过内容生产者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学习实现。将情境概念化为“游戏”有助于将注意力转移到情境中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利益、行动和权力流动上(Haapoja,Laaksonen & Lampinen,2020)。
其中,“算法可见性”是内容生产者成功的重要指标,是理解当前用户内容生产和“算法游戏”焦点的关键概念。“算法可见性”意味着被算法选择和加权,在平台中被赋予话语权和合法性(O’Meara,2019)。平台通过界面和算法管理用户活动,内容生产者则通过与平台编码环境的交互来影响自身的算法可见性(Van Dijck,Poell & de Wall,2018:9)。“算法游戏”的玩家需要遵循平台架构中嵌入的特定逻辑(Bucher,2012),即游戏规则,否则将面临隐形的威胁(Bucher,2018:84)。对于内容生产者来说,确保算法可见性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不仅影响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机会(Bishop,2019),还影响他们的社会参与过程。
2. 信息中介平台
信息中介作为信息共享、个人表达和集体讨论的平台,在公共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中介是信息经纪人,它可以通过过滤、分类和个性化相关的算法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流,从而影响媒体传播的有效性(Jürgens & Stark,2017)。信息中介,包括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内容聚合平台,可以帮助用户处理冗余信息,同时也改变了信息的可见性和呈现方式。
作为内容过滤工具,信息中介不可避免地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内容进行审核和优先排序,赋予某些内容更高的权重,并降低、更改或删除其他内容。内容在信息中介上的排名越高,用户实际看到并与之互动的可能性就越大(Mosseri,2016)。相反,算法排名较低的内容可见性较低,可能会因违反信息中介的规则而被删除。对EdgeRank算法的批判性分析表明,它是一种“自动的、预先确定的选择机制,它确定了相关性并最终划定了媒体空间的可见范围”(Bucher,2012)。因此,新闻选择的控制权正在从传统新闻机构进一步转移到平台,使后者迅速成为内容生态系统的中心节点(Van Dijck,Poell&de Wall,2018:50)。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中介并非中立的、纯技术的平台,控制内容可见性的算法及其内部运作仍处于“黑箱”状态(Bell,2015),从而引发“责任、程序和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Tufekci,2015)。事实上,内容生产者几乎无法控制平台的基础设施或管理逻辑,系统所有者和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构成了两者之间的权力鸿沟(O'Meara,2019)。一方面,出于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需要(Kitchin,2017),平台很少分享有关算法架构或工作原理的细节。另一方面,平台在实施内容审核或规范变更时,往往不提供事先通知或解释,而是在未经用户同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塑用户看到和参与的内容。
3. 平台家长制
“家长制”一词源于拉丁语pater,意为“父亲”,特指父子关系(Thomas,2016)。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有刷抖音浏览量的网址吗,1995)在分析保守派政治的道德隐喻时,提出了“严父模式”,即“父亲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道德约束,并通过自律和自我克制命令他人服从”。这种基于核心家庭的道德隐喻通常表现为家长制,即倾向于通过限制他人的主动性来阻止或干涉他人的行为,理由是被干涉者将受益或免受伤害(Baldwin,Brownsword & Schmidt,2009)(Appelgren,2017)。
在内容生产领域,平台权力的不断扩张催生了“平台家长制”的概念。平台在“算法游戏”中扮演家长的角色,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惩罚用户的违法行为,从而培育、展示和合法化其权力。对谷歌、Facebook、Instagram等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平台宣称以用户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单方面发布规则、声明和处罚,将“算法游戏”的参与者描述为道德离经叛道、不诚实的人,这不仅赋予了平台结构性和经济性权力,也赋予了平台道德权威(Petre,Duffy & Hund,2019)。基于此,Petre等(2019)提出了平台家长制的概念,即平台在内容治理中单方面发布规则、划定边界、施加惩罚,从而建立家长式权威。
随着中国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家长制倾向逐渐显现。但总体来看,平台家长制倾向虽然初步显现,但其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建构以及背后的运作逻辑尚不明晰。因此,本文旨在以“算法游戏”为理论视角,从媒介话语实践的角度洞悉中国语境中的平台家长制动态。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算法游戏”的话语建构采用了什么样的框架和主题策略?(2)这种建构如何为平台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话语资源?(3)这套话语实践背后呈现着怎样的平台家长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规范视角进一步明晰平台在内容生产监管中的权力边界,推动建立更加民主的内容生态和算法治理体系。
三
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
策略性选取的事件特别容易呈现出研究者感兴趣的社会现象(Petre, Duffy & Hund, 2019)。因此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选取信息中介平台内容治理的“热点时刻”,考察了微信、微博、抖音三大新媒体平台的内容治理行动,即“微信青峰计划”、“微博蔚蓝计划”和“抖音啄木鸟行动”。其中,抖音大量使用算法进行信息分发和监督,技术属性强于微信和微博。选取该案例有助于发现不同类型平台之间的差异。
话语体现着社会权力结构,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话语分析考察围绕“算法游戏”的媒体话语实践。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公开的话语,展现了其背后的权力是如何被固化、凸显和落实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平台家长制的话语建构与运作机制提供经验支持。
鉴于新闻媒体在建构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媒体报道为考察平台如何获取并维持符号权力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此外,由于平台工作的不透明性,平台发布的官方公告也是洞察平台运作的重要数据来源。笔者以“微信青峰计划”“微博蔚蓝计划”“抖音啄木鸟行动”为关键词,通过百度新闻、微信公众号、政府官网等多个渠道搜索,收集了所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告进行文本分析。截稿时间为2020年9月4日。经过人工筛选,共获得87篇文本材料作为研究样本。
2.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利用框架分析法识别围绕“算法游戏”的主导话语框架。借鉴William A. Gamson等(1989)的“媒体包”方法,本文重点分析了隐喻、例子、格言、描述和视觉形象五个框架元素。同时,本文引用David Altheide的定义来区分框架和主题——主题是典型的主题,在许多文本中反复出现,具有描述性;而框架是持续性的,是讨论特定事件的焦点、参数或边界(Altheide,1996:31),该定义用于定义和区分话语中的持续性框架和描述性主题。
接下来,本文通过开放编码、联想编码、选择编码三级编码程序对收集到的文本材料进行文本分析。这一阶段不仅关注话语的具体文本特征,更注重阐释叙事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兼顾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层面。通过深挖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与逻辑语境,最终提炼出平台家长制的运行机制。
四
平台家长制的话语建构:
“流量贬值”框架
研究发现,“算法游戏”的话语叙事呈现出一种“流量贬值”的道德框架。与Petre等(2019)的结论一致,相关媒体话语通过诉诸道德框架来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文化生产实践。但与北美语境中“真实性”的隐喻不同,“流量贬值”框架将流量斥为“黑心”,将其与“金钱”、“博眼球”等同起来。同时,它贬低了内容生产者对流量的追求,称其为“刷赞、刷粉、薅羊毛、引流诈骗等作弊行为”,其目的是篡改客户端数据逻辑,从而快速攫取一波流量并变现。正如腾讯相关负责人谈到“恶意营销的根源”时所说:“根源还是利益驱动,还是对粉丝和流量的追求。”(36氪,2020)
具体来说,“流量贬值”的框架围绕三个主题展开,每个主题都运用了不同的隐喻和文化资源进行阐释。第一是对立主题,主要运用了“猫捉老鼠游戏”、“羊毛派对”等隐喻;第二是生态主题,包括“垃圾”、“污垢”、“虫子”等环境隐喻;第三是合作主题,包括“共同努力,共克时艰”等探讨。在这样的主题叙事下,隐喻的特性被自然移植到本体中,从而赋予流量以及追逐流量的“算法游戏”玩家道德的贬值。
1. 对立主题:“猫和老鼠”的激烈对抗
“对立”首先是指“算法游戏”玩家与平台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包括日常的战略对抗和集中打击。在媒体话语中,打击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可分为违法犯罪行为和道德越轨行为两大类。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指诈骗、黑灰行业、发布违法信息等,道德越轨行为主要指平台定义的“算法游戏”玩家的诈骗作弊行为,如骗取点击、恶意引流、低俗炒作、地域攻击、封建迷信、夸大误导、谣言、明星黑粉、恶意跟风辱骂等,通常通过诱导分享、发布外链、使用外挂等方式进行传播。对此,平台不遗余力巡查打击,与“靠刷量作弊的黑产团伙”的对立持续存在”(北京商报,2019)。
除了强调“算法游戏”玩家与平台的对立,对立的主题也致力于塑造“流量”与“质量”的对立。“流量”作为“质量”的反义词出现,追逐“流量”意味着低质量。当自媒体围绕“注意力市场”结构,以“点击量”和“流量”作为诉求时,围绕质量、服务、创意、价格的竞争就变成了“流量竞争”,结果将是“乱象丛生、劣币驱逐良币”(环球网,2020)。因此,“流量乱象”强烈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仲裁者来引导和评判。
此外,对立主题也将“算法游戏”玩家与“一般消费者”对立起来,强调“算法游戏”玩家的“薅羊毛”行为会对消费者和平台的利益造成损害,甚至危及市场经济环境。“拉毛线党”隐喻的运用,不仅将“算法游戏”玩家与“占便宜”“侵犯公共利益”“违反公平正义”等道德内涵联系在一起,也将他们与普通用户区分开来,置于与社会大众的对立面。
在这场“猫鼠之战”(21世纪经济报道,2020)中,平台常常以公正的仲裁者身份出现,治理行动的紧迫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鼠是一个经典的反面形象,常常与偷窃、腐败、瘟疫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刘建龙,2020)。借用这个隐喻,“算法游戏”的玩家们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赋予了小偷小摸、追逐名利的反面形象。相比之下,平台则被定义为无私的仲裁者和惩罚者,其目的纯粹而单一,就是维护正义、惩恶扬善。平台公正无私,“不会为了虚假的粉丝和阅读量繁荣而对所谓的大V、大账号视而不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贡献。 与“算法游戏”玩家“斗智斗勇”已成为常态(北京商报,2019),因此,对立主题不仅从道德立场对“算法游戏”玩家进行指责,也赋予平台内容治理行为充分的合法性,赋予其家长式的权威。
2. 生态主题:乌托邦的生态隐喻
如果说对立主题的叙事充满斗争与对抗,那么生态主题则充满和谐、纯洁、美好的意象。生态主题通过援引蓝天、绿植、自然环境等各种被净化的生态隐喻,将网络空间理想化为纯净、无污染、极其美好的精神家园。如信息中介平台“致力于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让网络空间清朗、生态(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0)。微信、微博、抖音三大平台推出的专项行动均以生态主题命名,微信的“青风计划”意为“积极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微博的“蔚蓝计划”意为“共同捍卫微博的蓝天”(蓝鲸传媒,2019),抖音“啄木鸟行动”意为清除网络空间的白蚁。
这样的表态反过来又进一步合法化了平台的惩罚行为,强化了其惩罚的权威性。因为“算法游戏”玩家的行为是肮脏、危险、有毒有害的垃圾或污垢,他们是“破坏良好网络舆论生态”的罪魁祸首,是平台清理整顿的对象。在强烈的反差冲击下,平台的震慑力和执行力被不断强调。比如微信对违规者采取阶梯式处罚规则,屡次、严重或多次违规将被给予更重的处罚(微信110,2020)。“对于这些垃圾信息,我们似乎只有被动的接受……只能寄希望于管理平台能还消费者一片碧水蓝天”(网易新闻,2020),类似的表态赋予了平台绝对的“严父”形象和内容生态治理的唯一合法性。
在严厉打击不良内容的同时,平台还“致力于打造绿色、安全、健康的平台环境”(新浪财经,2020),“鼓励内容作者创作优质内容”(澎湃新闻,2020)。但对于“优质内容”的定义,却没有明确,只有“正确引导、正面宣传”、“积极健康、向上善良”或“积极传播正能量”等一些模糊的描述。可见生态主题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虽然平台的内容治理行动通过生态隐喻与自然生态的想象相联系,但仍然缺乏具体实施细节和具体要求,为平台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三)合作主题:风险共担、责任稀释
相较于自利,合作被普遍认为是互联网经济更为重要的特征(Benkler,2011),合作共享理念也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话语资源。
在合作主题中,“多方共治”“携手攻坚”“合作治理”等话语,以合作隐喻的方式,从道德视角传递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合作愿景,凸显平台治理的道德优势。例如,“互联网生态治理是一场硬仗,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蓝色计划》,2020a)。这一主题凸显了“算法游戏”参与者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所需的治理成本,“打击黑色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蓝色计划》,2020b)。责任方不仅限于平台本身,还包括“公安司法机关、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银行、通信运营商、广电、互联网企业、学术界和广大网民”(《香江晨报》,2020)。 因此,这一主题将各界责任主体定义为合作伙伴、战友、利益共同体,用道德诉求实现责任划界、风险共担。同时,合作的主题也间接凸显了平台治理行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因为它符合公众利益和共同期待,能够“增进全社会福祉”(南宁市网警巡警执法队,2020),同时又避免了平台作为商业企业背后的逐利动机。
其中,特别强调网民监督举报和社会参与,如“需要广大网民同心协力,积极举报,共同推进网络安全建设”(蓝色计划,2020b),就是试图通过公众参与弥补平台制度保障的不足。这种倡导“用户标签化”的做法具有强烈的“动员式治理”特征,其逻辑在于强调广泛的群众参与以克服监管资源的匮乏(易前良、唐芳云,2021),并由此淡化背后的企业责任和义务。
五
平台家长制的运作方式:
自律、移植与主导秩序
“流量贬值”框架及其下的三大主题共同塑造了平台内容生产的边界,其背后的自律、移植和显性秩序三种运行机制是平台家长式话语实践的深层逻辑。
1. 自律:国家赋权下的平台自律
与西方国家“自治”或“自律”的平台治理模式不同,中国语境下的新媒体平台治理是一种授权式的自我监管,或者说是政府监督下的行业自律,介于法定监管与自律之间(张文峰,2015:116)。国家与平台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线性关系,而是基于政权的授予和代理,通过“自律”的机制来实施。这样的权力关系淡化了官“纪”的色彩,暗中激活了平台家长制的运作。
关于平台治理,学界主张将公平、问责、透明、伦理和责任等原则纳入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中(Diakopoulos et al.,2016)。在宣传新闻理念的引领下,正确的导向因素成为中国语境下平台媒体的算法价值,有别于西方(王倩,2020)。2020年3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基本形成了国家、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治理模式。其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核心,平台治理“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新华网,2020)。而到了地方实施,则与地方机构形成的网络息息相关。 地方公安局、网信办、文化执法队等主体构成以地方政府为代表机构的政府间网络,是落实监管政策的重要行为主体(刘锐、许景宏,2018)。例如,“广东牢牢把握强化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这个关键环节,及时督促地方重点网站平台对标《条例》要求”(潇湘晨报,2020)。
互联网平台从“外部监管”转向“自我监管”,凸显了国家角色的变化,也是国家与平台权力关系变化的体现。国家从“控制—指挥”型的监管者转变为“协调者、整合者”(刘锐、许景宏,2018)。内容治理的权力被下放到平台本身,平台对自媒体乱象的滋生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平台被定性为“自媒体运营的服务者、自媒体行业秩序的维护者”,需要“积极履行平台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网络传播杂志,2019)。 《规定》为平台权力的获取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表明平台有权“通过服务协议等方式与用户约定平台管理规则”,通过“深入自查自纠”的自律模式进行自我监管(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0)。国家的权力赋予为平台的治理自主提供了支撑,平台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化、法制化。但这种“自律型”治理模式高度依赖平台的自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固有的“黑箱”性质,进一步加剧了平台的家长式倾向。
2.移植:技术神话的延伸与调用
算法转向预示着日常生活的数字化。算法处理与数据成为一种新兴的权力与知识生产机制(Wenz,2013)。现代科技神话不仅是科技的符号化表达,也体现了民众对新技术的潜意识并赋予其合法性,更是塑造科技社会功能与社会意义的话语行动(刘海龙,2017)。全社会数字化的快速推进与不断强化的技术合法性叙事相互融合,成为一股不断渗透进人们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在此趋势之下,“算法游戏”的话语建构采取了“移植”的逻辑,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算法技术的合法性,还将这种合法性嫁接到技术拥有者——平台本身身上,共同捍卫平台家长制的权威。
“移植”首先反映在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中,以确定非法的内容生产者和内容,尽管引入了“信息中间”,但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审查”,但仍在使用“技术审查”和“脉络” conforce'和继续努力,但仍在使用自动检测技术我们的SESE意味着技术的合法性和手动审查的缺陷。
虽然扩大了技术神话的合法性,但“算法游戏”的话语也借用了技术神话的合法性,以服务于平台家伙的运作。相关的话语尤其强调平台使用技术手段来识别和管理有害行为,例如“依靠算法来传达指导和智力来领导价值”(互联网交流杂志,2019年,与Wechat和Weibo, 抖音相比,它具有更明显的技术属性,从而强调了其自身的技术效果使技术和算法成为促进平台行为规范的重要治理工具,然后认可平台内容治理的合法性和合法性。
3.主导顺序:平台兴趣偏好作为游戏规则
为了回应算法可见性,用户和平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功率差距。
平台自己的商业兴趣偏好是一个重要的“算法游戏”规则,首先通过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通过服务协议的结论和其他方式,在平台管理规则上与用户进行了直接调节用户的权力,以实现“每日监督”的规定,并在平台上进行阶段的规定,并将其依据。但是,在法律依据中,伊斯尼亚岛和特殊的治理行动都有在法律依据的余地,而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恶意指导流量”,“以公共秩序的方式进行严重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王子的效果和价值观,使王子的效果和价值观构成。平台家长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结果,信息中间平台已成为内容生产的中心节点,不仅参与内容生产,而且还拥有内容生产者的“生与死力量”。
作为“算法游戏”的重要兴趣,内容生产者在媒体话语中已成为无情的对象,并且在平台的主导地位的底部是纠正的。他们对平台的内容治理的看法和反馈是极为罕见的。
六
总结
信息中间平台的公共性质越来越突出,确定谁将确定公共信息的筛选标准(Just&Latzer,2017年)。围绕平台和内容生产者之间的算法形成。
遵循Petre等人(2019年)的研究,将“使用算法”扩展到“算法游戏”的权力关系中。 ”。 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媒体话语实践背后出现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和游戏规则,然后批评算法的力量和平台力量,进一步阐明了中国背景下平台家长式主义的权力动态和操作机制。
Wendy Espeland等人(1998年)强调,它们是政治性的,它们重建权力关系,建立新的政治实体,并建立新的解释性框架。首先,平台的家伙。对薅羊毛和兴趣的追求贬低了“算法”玩家的道德含义,2019年)。 其次,建立平台的道德权威有刷抖音浏览量的网址吗,并将信息平台定义为无私的中性和仲裁,而在心理上是可谴责的“算法游戏”,平台代表了大多数用户,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生态的公共利益算法的所有者设定了游戏的每日规则,同时也可以通过“交通偏差”的话语框架,设置和强制实施严格的道德界限,并进一步建立了其权威,并实现了更高的范围,从而,信息中间平台惩罚了用户的强大权威。
在中国的背景下,“交通”和“追求交通”是自然而然的,该平台与政治力量,科学和技术神话交织在一起,并且通过自我差异,自我差异,移植的机制来促进其自身利益,并削弱了公众的兴趣,并促进了公众的兴趣,从而使其越来越多。 ,2017年的比较,具有更强的技术属性的平台通过科学和技术神话移植的逻辑发展平台更倾向于养育遗产。
有趣的是,平台对中间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域流程“作为道德铁路,以及平台功能区域的SO公共领域流量”,例如搜索列表和内容建议。 - 粉丝 - 用户 - 乘法“粉丝经济模型和“ dou+”以增加视频播放量,所有指导用户为平台的促销服务付费。隐含的逻辑是,向平台支付是唯一改善算法的法律渠道。可以预见的是,“流量的退化”将深深地影响“算法”的范围,并进一步构建了“算法”和“进一步的平台”,并进一步启动了glegor的范围。
此外,李·扬港(Li Yanhong)的界限在哪里,李·扬港(Li Yanhong)的宣传和平台的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liu rui,xu jinghong,2018年)参与监督和利益相关者(Gorwa,2019年)。内容审核需要在内容创建自由和平台规则之间不断权衡,以及平台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滥用算法和平台霸权。
这项研究中有几个缺陷,在随后的研究,练习,行动等中尚待改善。
本文是一个简短的版本,省略了参考文献。
封面图片来自互联网
这一问题的执行/Xiao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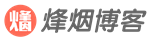 短视频热门教程
短视频热门教程
发表评论